16%的美国作家有意回避争议话题
自我审查为何比监控更可怕
○作者 [美] 大卫·尤林 ○译者 陈荣生
《
青年参考
》(
2013年12月11日
32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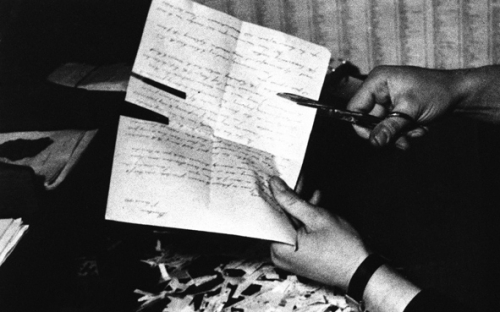 |
|
对作家而言,比政府监控更危险的,是这种监控导致的自我审查。
今年11月,“美国笔会中心”公布了一篇题为《寒蝉效应》的报告,其中的一些数据令人不安——是关于政府监控对文学界的言论自由和自我审查的影响的。对520多位美国作家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16%的人在写作中曾有意回避被认为存在争议的话题,还有11%的人“考虑过这样做”。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进行调查时,相应比率更高。
尽管我毫不怀疑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机构的监控给言论自由带来了寒意,更不怀疑作家们的日常通讯已经遭到监控,《寒蝉效应》提出的真正问题,实际上跟勇气有关。
毕竟,文学向来被认为是有风险的领域。文学要求我们去挖掘,去思考我们真正感受和经历过的事物,去探索复杂性、细微差别、灰色地带、人类渴望的以及害怕的东西。
声名显赫的作家通常都被视为麻烦制造者:沃尔特·惠特曼、威廉·巴勒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乔纳森·斯威夫特……他们从不因害怕成为攻击目标而裁减写作素材,他们写的就是他们心里想说的——政治性的或非政治性的,挑战对规则的服从,挑战内心的软弱。
这让我想起了托马斯·潘恩。1776年,他不得不匿名出版《常识》一书。在当时看来,该书的论据是极为“大逆不道”的。再就是哈丽特·比彻·斯托,她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在导致美国南北战争的废奴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拉德克利夫·霍尔、约翰·雷奇、保罗·莫内特等,他们的作品促成同性恋文化融入了现代生活的主流。
1995年2月,莫内特死于艾滋病。此前数年,他对我说过:“我们全都是萨尔曼·拉什迪,我们全都是安妮·弗兰克……我们必须确保前辈们的文采不被后世忘却,而且还要设法让自己获得足够的文采,以说服与我们同时代的人,并告诉后人我们是谁。”
是的,历史之舟,是书籍扮演的最重要角色,它让人们能够跨代沟通,能够看到自身认知和理念的进步。书籍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是通过把我们直接推进它们的创作者的头脑中,让我们处于他们的信念、情感以及他们体验世界的方式的影响下达到的。
理解了这一点,你的思想就会产生飞跃,你将认识到:一切都是相对的,现状,即我们习以为常并接受的法律、道德、习俗,既不是对的也不是错的,不过是一种路径罢了。
这也说明了审查令人憎恶之处——它戕害了言论自由的信念。在我看来,任何审查都比不上自我审查更可恶,因为,后者让我们与身为作家应该反对的事情成为同谋。
我不是说,书籍本身不会向特定方向诱导读者,事实上,这正是它们吸引人的一种方式。我童年时被文学吸引,是因为它给我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感受方式;否则,我就无法拥有这种感受,即使日后与之偶遇,可能也要付出更大代价。
我也不是说,世上没有坏书、唯利是图的书、讲述人类阴暗面的书以及暴露我们的偏见和恐惧的书。《我的奋斗》之类的“名著”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然而,我依然会捍卫它们的生存权,甚至是它们的被阅读权,因为这是言论自由需要的。
“你不可能通过压制而消灭某种思想,”亨利·米勒如是说,“与这个问题有联系的一条法则,就是你应当能够自由阅读自己选择的东西。换言之,无论作品对其是好是坏,作为个体的阅读者都有选择的自由。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邪恶,又怎么可能远离邪恶?”
基于上面这一切,今天的美国作家有两个选择:逃避或挺身而出。
我可以像某位匿名作家在报告中提到的那样,“我正考虑写一部有关核战争的书……阅读了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报道后,我决定把这个想法放到一边,因为,如果我用谷歌搜索‘核爆炸’、‘防空洞’、‘辐射’、‘秘密计划’、‘武器装备’等,某些人会有什么看法呢?”
或者,我也可以以威廉·沃尔曼为榜样。联邦调查局一度认定他是恐怖分子,面对来自政府的压力,沃尔曼果断将联邦调查局告上法庭,随即将此事通过媒体公诸于众。
我曾经评析过捷克前领导人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政治生涯及其提出的“第二文化”观念。在后一个观念中,自由被定义为“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是自由的一种功能”。这是一个重要概念,告诉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到头来,保护我们的权利的还是我们自己。
从这一点上,我也看到了美国笔会中心的这份报告所揭示的最令人心寒的方面:不是因为监控本身多么邪恶,而是因为有一些作家选择了屈服。
□美国《洛杉矶时报》

对作家而言,比政府监控更危险的,是这种监控导致的自我审查。
今年11月,“美国笔会中心”公布了一篇题为《寒蝉效应》的报告,其中的一些数据令人不安——是关于政府监控对文学界的言论自由和自我审查的影响的。对520多位美国作家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16%的人在写作中曾有意回避被认为存在争议的话题,还有11%的人“考虑过这样做”。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进行调查时,相应比率更高。
尽管我毫不怀疑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机构的监控给言论自由带来了寒意,更不怀疑作家们的日常通讯已经遭到监控,《寒蝉效应》提出的真正问题,实际上跟勇气有关。
毕竟,文学向来被认为是有风险的领域。文学要求我们去挖掘,去思考我们真正感受和经历过的事物,去探索复杂性、细微差别、灰色地带、人类渴望的以及害怕的东西。
声名显赫的作家通常都被视为麻烦制造者:沃尔特·惠特曼、威廉·巴勒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乔纳森·斯威夫特……他们从不因害怕成为攻击目标而裁减写作素材,他们写的就是他们心里想说的——政治性的或非政治性的,挑战对规则的服从,挑战内心的软弱。
这让我想起了托马斯·潘恩。1776年,他不得不匿名出版《常识》一书。在当时看来,该书的论据是极为“大逆不道”的。再就是哈丽特·比彻·斯托,她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在导致美国南北战争的废奴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拉德克利夫·霍尔、约翰·雷奇、保罗·莫内特等,他们的作品促成同性恋文化融入了现代生活的主流。
1995年2月,莫内特死于艾滋病。此前数年,他对我说过:“我们全都是萨尔曼·拉什迪,我们全都是安妮·弗兰克……我们必须确保前辈们的文采不被后世忘却,而且还要设法让自己获得足够的文采,以说服与我们同时代的人,并告诉后人我们是谁。”
是的,历史之舟,是书籍扮演的最重要角色,它让人们能够跨代沟通,能够看到自身认知和理念的进步。书籍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是通过把我们直接推进它们的创作者的头脑中,让我们处于他们的信念、情感以及他们体验世界的方式的影响下达到的。
理解了这一点,你的思想就会产生飞跃,你将认识到:一切都是相对的,现状,即我们习以为常并接受的法律、道德、习俗,既不是对的也不是错的,不过是一种路径罢了。
这也说明了审查令人憎恶之处——它戕害了言论自由的信念。在我看来,任何审查都比不上自我审查更可恶,因为,后者让我们与身为作家应该反对的事情成为同谋。
我不是说,书籍本身不会向特定方向诱导读者,事实上,这正是它们吸引人的一种方式。我童年时被文学吸引,是因为它给我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感受方式;否则,我就无法拥有这种感受,即使日后与之偶遇,可能也要付出更大代价。
我也不是说,世上没有坏书、唯利是图的书、讲述人类阴暗面的书以及暴露我们的偏见和恐惧的书。《我的奋斗》之类的“名著”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然而,我依然会捍卫它们的生存权,甚至是它们的被阅读权,因为这是言论自由需要的。
“你不可能通过压制而消灭某种思想,”亨利·米勒如是说,“与这个问题有联系的一条法则,就是你应当能够自由阅读自己选择的东西。换言之,无论作品对其是好是坏,作为个体的阅读者都有选择的自由。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邪恶,又怎么可能远离邪恶?”
基于上面这一切,今天的美国作家有两个选择:逃避或挺身而出。
我可以像某位匿名作家在报告中提到的那样,“我正考虑写一部有关核战争的书……阅读了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报道后,我决定把这个想法放到一边,因为,如果我用谷歌搜索‘核爆炸’、‘防空洞’、‘辐射’、‘秘密计划’、‘武器装备’等,某些人会有什么看法呢?”
或者,我也可以以威廉·沃尔曼为榜样。联邦调查局一度认定他是恐怖分子,面对来自政府的压力,沃尔曼果断将联邦调查局告上法庭,随即将此事通过媒体公诸于众。
我曾经评析过捷克前领导人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政治生涯及其提出的“第二文化”观念。在后一个观念中,自由被定义为“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是自由的一种功能”。这是一个重要概念,告诉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到头来,保护我们的权利的还是我们自己。
从这一点上,我也看到了美国笔会中心的这份报告所揭示的最令人心寒的方面:不是因为监控本身多么邪恶,而是因为有一些作家选择了屈服。
□美国《洛杉矶时报》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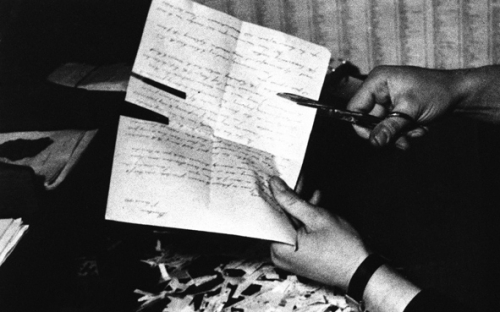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