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
要态度不要原则:知识分子通病?
○作者 [美] 托马斯·索维尔 ○译者 张亚月 梁兴国
《
青年参考
》(
2013年12月11日
33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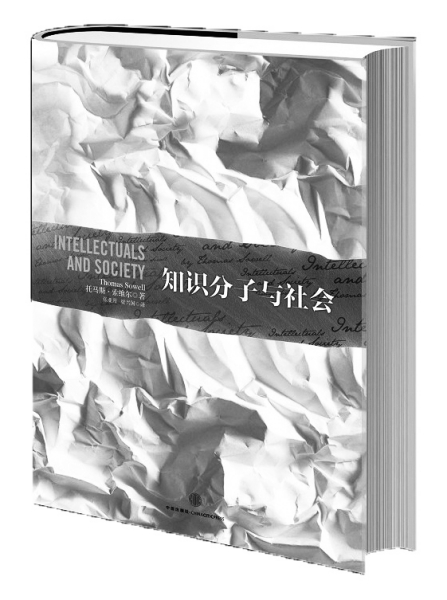 |
|
当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以态度而非原则指导自身言行,他们就离公众期待渐行渐远。
理想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工作建立在特定原则的基础上——逻辑原则、证据原则,也可能是道德原则或社会关怀原则。不幸的是,在公众对他们的期待之下,知识分子实际上不一定会这样做。态度,而非原则,往往在引导知识分子时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知识分子总是乐意去说,或者去做与原则无关而与态度大有关系的事情。他们愿意接受这样一些人的减刑主张,如声称被妻子折磨的谋杀犯,或是据说有过创伤性童年经历的罪犯,又或是普遍意义上的不幸者。但正是这些貌似慈悲为怀的知识分子,很少对警察的行为表示宽容,而后者时常要在以自身性命为代价的千钧一发之际,做出攸关生死的抉择。
黑人群体的领袖对亚裔商店主人进行种族主义攻击时,甚至对白人和犹太人做出类似举动时,一些曾经反对种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不是保持沉默,就是为这种言行辩护。同样,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大力谴责公司高管的“贪婪”,但高管们的收入通常仅为职业运动员和娱乐明星收入的一部分,而那些明星很少——若不是从未——被指责为贪得无厌。
每当石油公司的利润增加,知识分子就会发起愤怒的抗议,尽管每加仑汽油中的利润份额低于税收份额。在美国,“贪婪”的概念几乎从来不被适用于政府部门,无论是就其所课税收的数量,还是其对工人阶级的苛刻,知识分子都很少表示异议。高额税收经常呈现出这样一种现象:人们终其一生的劳动所得,都被为了某个地区的“再发展”而大规模没收。通过“再发展”,政府又可以获得更多税源,更多的税收又令政客们有更多钱投入选战。
知识分子的过激反应或麻木不仁,不仅说明其言行更多地与态度有关而与原则不大相关,且经常演变为将态度凌驾于原则之上。这些偏见并不局限于对特定人群,甚至会延伸到概念层面,比如对“风险”的多重评判标准。
知识分子强烈批评某些临床医药可能产生的风险,认为政府有责任禁止生产这类药物。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这些人,从来不会呼吁政府禁止高空速降和独木舟漂流,尽管后两者往往意味着更高的风险,而且只是为了寻求刺激——相比之下,有风险的医药至少是为了击败病痛而诞生。同样,每当有拳击手死于赛台,必定会激发知识阶层和媒体关于禁止拳击的呼声;而在滑雪事故导致死亡之后,他们并未提出相同的要求——哪怕死于滑雪的人更多。
尽管不同个体的态度通常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知识分子群体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群体意识(或群体无意识)的产物。此外,这些态度往往随着时间发展而集体性地改变,成为一个个年代中的过眼云烟,根本无所谓永恒不灭或放之四海皆准。
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在20世纪早期的进步主义时代,种族和少数族裔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消极词汇,对优生学的支持,某种程度上具有“可取性”,从而导致社会有意阻止特定种族和少数族裔过多地繁殖同类。众所周知,这种气氛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基本过时,少数族裔一跃成为格外受照顾的对象。60年代以后,对少数族裔的关切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强迫症,尽管它与此前几十年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罹患的强迫症截然相反。
在更早的时期,农民和工人是受到特别关切的焦点。彼时,并没有谁注意到,为这些群体谋取的利益可能会给少数族裔或其他人群带来不利影响。同样,在后来的日子里,知识分子也几乎从不关注少数族裔和妇女的反歧视行动可能对其他人不利。
没有什么规则可以说明这些集体性的情绪转变,受到特别关切的对象不断变幻,似乎只是定期更换的吉祥物。这像不像青少年的潮流偶像?今天是时髦的标志,明天就被“弃之如敝履”。
□节选自《知识分子与社会》,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

当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以态度而非原则指导自身言行,他们就离公众期待渐行渐远。
理想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工作建立在特定原则的基础上——逻辑原则、证据原则,也可能是道德原则或社会关怀原则。不幸的是,在公众对他们的期待之下,知识分子实际上不一定会这样做。态度,而非原则,往往在引导知识分子时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知识分子总是乐意去说,或者去做与原则无关而与态度大有关系的事情。他们愿意接受这样一些人的减刑主张,如声称被妻子折磨的谋杀犯,或是据说有过创伤性童年经历的罪犯,又或是普遍意义上的不幸者。但正是这些貌似慈悲为怀的知识分子,很少对警察的行为表示宽容,而后者时常要在以自身性命为代价的千钧一发之际,做出攸关生死的抉择。
黑人群体的领袖对亚裔商店主人进行种族主义攻击时,甚至对白人和犹太人做出类似举动时,一些曾经反对种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不是保持沉默,就是为这种言行辩护。同样,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大力谴责公司高管的“贪婪”,但高管们的收入通常仅为职业运动员和娱乐明星收入的一部分,而那些明星很少——若不是从未——被指责为贪得无厌。
每当石油公司的利润增加,知识分子就会发起愤怒的抗议,尽管每加仑汽油中的利润份额低于税收份额。在美国,“贪婪”的概念几乎从来不被适用于政府部门,无论是就其所课税收的数量,还是其对工人阶级的苛刻,知识分子都很少表示异议。高额税收经常呈现出这样一种现象:人们终其一生的劳动所得,都被为了某个地区的“再发展”而大规模没收。通过“再发展”,政府又可以获得更多税源,更多的税收又令政客们有更多钱投入选战。
知识分子的过激反应或麻木不仁,不仅说明其言行更多地与态度有关而与原则不大相关,且经常演变为将态度凌驾于原则之上。这些偏见并不局限于对特定人群,甚至会延伸到概念层面,比如对“风险”的多重评判标准。
知识分子强烈批评某些临床医药可能产生的风险,认为政府有责任禁止生产这类药物。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这些人,从来不会呼吁政府禁止高空速降和独木舟漂流,尽管后两者往往意味着更高的风险,而且只是为了寻求刺激——相比之下,有风险的医药至少是为了击败病痛而诞生。同样,每当有拳击手死于赛台,必定会激发知识阶层和媒体关于禁止拳击的呼声;而在滑雪事故导致死亡之后,他们并未提出相同的要求——哪怕死于滑雪的人更多。
尽管不同个体的态度通常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知识分子群体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群体意识(或群体无意识)的产物。此外,这些态度往往随着时间发展而集体性地改变,成为一个个年代中的过眼云烟,根本无所谓永恒不灭或放之四海皆准。
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在20世纪早期的进步主义时代,种族和少数族裔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消极词汇,对优生学的支持,某种程度上具有“可取性”,从而导致社会有意阻止特定种族和少数族裔过多地繁殖同类。众所周知,这种气氛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基本过时,少数族裔一跃成为格外受照顾的对象。60年代以后,对少数族裔的关切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强迫症,尽管它与此前几十年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罹患的强迫症截然相反。
在更早的时期,农民和工人是受到特别关切的焦点。彼时,并没有谁注意到,为这些群体谋取的利益可能会给少数族裔或其他人群带来不利影响。同样,在后来的日子里,知识分子也几乎从不关注少数族裔和妇女的反歧视行动可能对其他人不利。
没有什么规则可以说明这些集体性的情绪转变,受到特别关切的对象不断变幻,似乎只是定期更换的吉祥物。这像不像青少年的潮流偶像?今天是时髦的标志,明天就被“弃之如敝履”。
□节选自《知识分子与社会》,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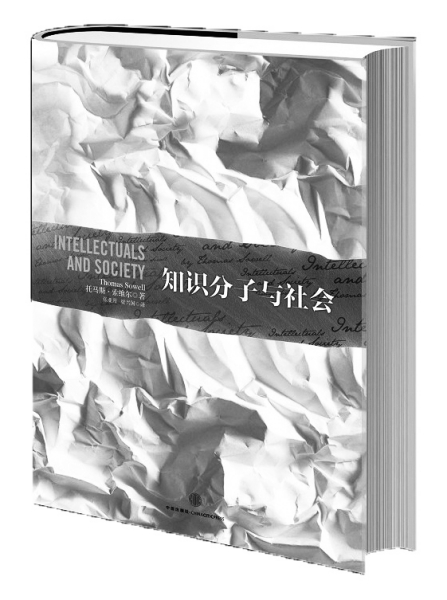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