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随时可能粉身碎骨,拆弹部队的词典中没有“退缩”这个字眼。从二战时的伦敦到21世纪的伊拉克,他们是智勇兼备的精英,承受着远超普通军人的磨难。
1940年,伦敦,英国陆军工兵拆弹部队的特伦斯·史蒂文森上尉挤出人群、越过封锁线,准备拆除废墟中的一枚定时炸弹。几英尺外,一位在先前轰炸中受伤的小伙子动弹不得,他只好安慰吓坏了的后者,说只是要取走炸弹的“扁桃体”,所以“不能乱说话”。史蒂文森每前进一步,都会通过麦克风与队友联系,他们在安全区紧张地注视着一切。
“先生,”小伙子不解地发问,“你在跟谁说话呢?”
“跟我的朋友们,”史蒂文森轻松的语气中隐藏着冷静,“告诉他们我在做什么。如果我干了什么蠢事,他们就可以教训我的接班人,那个倒霉蛋究竟哪里做错了。”
这是米高梅电影公司镜头下的一个经典场景。最终,史蒂文森有惊无险地拆掉了炸弹,还在弹壳上漫不经心地吻了一下。《塔尔图历险记》(1943)由此获得票房开门红。
当时,英国拆弹部队士兵参战后的平均寿命为10个礼拜。因拆弹失败而被炸得粉身碎骨属于常态。然而,没有谁因畏惧而退缩。“这是英雄的时代,是将个人勇气体现得淋漓尽致的时代,”一位军史专家断言,“在这个阶段,由于任务的紧迫性和缺乏知识储备与优良装备,不可思议的冒险成为必须,为的只是让更多无辜者逃脱死神。”
同炸弹“鼻尖对鼻尖”
布莱恩·卡斯特尼尔在其《漫长之路》一书中解释说,对于21世纪的拆弹专家们而言,类似的评价不显得过时,“许多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就是历史的支点。”卡尼斯特尔的感悟来自伊拉克战争,那也是他自己的战争。
卡斯特尼尔认为,在伦敦大轰炸期间,拆弹专家的智谋“最终改变了战争的方向。”相比之下,在伊拉克,“我们尚未开始就差不多失败了——进军巴格达途中,美军忘记了摧毁众多毫无防守的军械库,结果让那些军火被反美武装分子掠走并重新投入使用,埋藏在路边,让卡斯特尼尔和爆炸物处置部队的兄弟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生死考验。
二战时期的前辈们很少接受长期系统训练,手头只有简陋的铁锤、凿子和滑轮组,今天的拆弹部队已配备遥控机器人,最大限度地减少与炸弹的直接接触。的确需要真人亲自出场时,卡斯特尼尔们会穿上80磅重的铠甲:“谁都不敢轻松地走过这条漫长的路。只有各种选择都行不通了,只有机器人失败了才会……这是最后的选择,一直都是。”
佛罗里达州艾格林空军基地,有一所战地爆炸物处置学校,在那里经过高度仿真的严酷训练后,过关者才会被授予“爆炸物处置部队”徽章。与冷酷无情的炸弹“鼻尖对鼻尖”的对决,是对勇气和智慧的终极挑战,也是团队精神闪光的舞台,其中充满悬念和出人意料的可能性,很受作家和电影人喜爱,影片《拆弹部队》获奖显得理所当然。
血与火的记忆无法背叛
然而,正如卡斯特尼尔回忆录的副题《一个关于战争和战后生活的故事》所暗示,成功拆除一枚炸弹往往只是故事的序章。在用引人入胜的语言详细描述拆弹任务巨大危险性的同时,他也展现了爆炸物处置部队在炸弹不幸引爆后从事的工作,花费的时间与防止爆炸所耗费的几乎相同。许多时候,他们的努力显得劳而无功,这些努力大多发生在人间地狱般的袭击现场:“燃烧的汽车零部件……刹车油、支离破碎的手指、轴承、衣物碎片……苦苦寻找生命迹象。”
对于喜欢当代战争文学的读者而言,本书不严格遵循时间顺序的风格并未构成太大障碍。作者的核心思想很明确:拆弹部队生存的秘诀,就是把一切状况设想成最糟。
但是,到了和平时期,这种过度的警惕心和危机意识就转化成了沉重的负担,这在卡斯特尼尔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回到故乡,他依然感受到敌人虎视眈眈,妄想刚出生的儿子会惨遭杀害,整夜整夜地守在屋门外:“我坐在楼梯顶部,手持来复枪,在黑暗中等待。”这支来复枪总是打开保险,和在伊拉克时别无二致。“我处在危险中,我是孤独的,被外界孤立、包围和窒息。如果有必要,我会毫不犹豫的杀出血路……紧紧抓住来复枪,它就在我的肩膀上……当右手握住熟悉的枪柄时……狂乱的心情才能稍微平复。”
在家人悉心抚慰下,卡斯特尼尔的焦虑慢慢消散了。不过,要彻底背叛有关战争的记忆,仍然是一个不太可能成真的、尚未写就的故事。事实上,卡斯特尼尔用了很大的勇气才敢面对那段记忆,就如同他无数次在任务现场,面对带电的炸弹保险丝那般。
□美国《纽约时报》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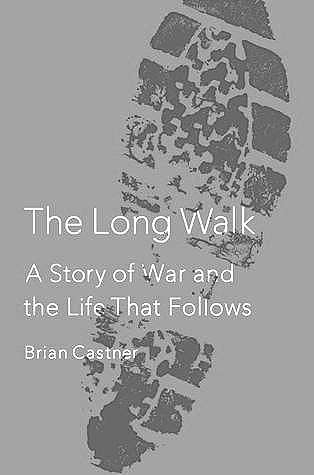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