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禽走兽懂得用音乐传递情怀,而今,它们伟大的“管弦乐团”正面临无以为继的危险。
你不必专程前往动物园,只需在离家不远的生态保留地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有贝斯手在轻抚琴弦,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倾诉着情话;偶尔会发现气得发抖的长笛演奏家,一心盼着双簧管演奏者能跟上他的曲调;还有许多风格各异的乐手,或秉性温柔或骄横跋扈,大家都有擅长的乐器。这就是伯尼·克劳斯在新书《伟大的动物管弦乐团》中向你揭示的秘密:飞禽走兽懂得用音乐传递情怀,而今,它们伟大的“管弦乐团”正面临无以为继的危险。
身兼博物学者和音乐家的克劳斯历时多年,收集了大量的野外声音,然后用文字将其重现,引领读者通过大自然馈赠的珍宝,意识到动物的音乐才能以及乐曲背后的故事。
在克劳斯的世界里,声音就好比一个精致的滤镜,可以帮你更清楚地看世界。这部无所不包的书中详述了各种声波的差别:海浪冲击海滩的嗡鸣;露水引致的回响;白天和夜晚的传音性;沙漠发出的咯咯声;我们还能读到狒狒怎样巧妙地利用花岗岩的回声,让自己的嗓音传至密林深处。在大开眼界、拓宽思路的同时,作者还试图让读者感受到声音所蕴含的情感变化。为此,克劳斯给一座正在经历变化的森林做了“声音日志”。也许,那片森林的表象依然繁茂,但音景已透露出了它被摧残的本质,那是来自大自然心底的挣扎。
人类是音乐世界惟一的主宰吗?克劳斯用大量章节论证:在野外,动物们有着胜似音乐家的鉴赏力,它们更能理解生态系统的倾诉,进而为寻找不同“发声位”而努力:“每个本地物种都获得了自己的首选声音波长,随后进行混音或和声。它们在自然界的发声位有如小提琴、木管乐器、小号和打击乐器在管弦乐团里那样,彼此应和而互不相扰。”
克劳斯的假说包含非凡的论点:生物栖息地环境越好,富有音乐表现力的物种就越多,它们的音阶变化就越丰富,音域也越宽广。声音的复杂性可用来判断环境的健康程度。同为音乐家,本人对乐感至上的论调无法赞同。但克劳斯显然是个不吝于论断的人:他大胆批评说,所有的西方音乐都止步不前,缺乏“真正与自然界的有机联系”。
动物们需要音乐来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尤其复杂,让克劳斯探索不倦。他援引的研究结果显示,“雄性长臂猿为成功吸引异性,它们的歌声很少重复,却又遵循严格的转调方式和表达形式。”音乐的具体功能则令人大开眼界:雌性大猩猩在梳洗时,如果受到雄性大猩猩“大声尖叫”和“捶胸”声的惊吓,便借助“唱歌”以平静心绪;蟋蟀通过调节鸣叫速度来表达温度高低;蟾蜍用齐声合唱来迷惑敌人,让对方搞不清每一只的具体位置。
那个关于蟾蜍的例子最令我心碎:每当喷气式飞机飞过天空,它们就不再同步发声。这临时搭建的声音迷宫一旦被摧毁,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老鹰的袭击。换言之,蟾蜍的音乐是它们的庇护所。通过不少类似的故事,克劳斯为我们勾勒了一副深具讽刺意味的画面:人类为自己建立安乐窝而远离自然,与此同时,我们把在文明出现前的音乐也关在了门外——这些背景音曾是我们保护自身、享有平和与快乐的所在。现今,我们离它们渐行渐远了。
有感于克劳斯传诉的情怀,我想到了被尊为“有深度的倾听者”的查尔斯·艾夫斯。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查尔斯和克劳斯一样,都有重要的东西想表达,但他面对的却是个不愿倾听的社会,只是被人们视作过度敏感。文字间透出失望之余,难免有几分惆怅。
在地铁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刚合上这本书,就瞧见了一个小女孩,她正冲我微笑,大大的眼睛里满是探寻的目光。而在我们做无声的交流时,女孩的妈妈在旁闭着眼睛,沉浸在耳机中的世界里,即使震耳欲聋的列车在一旁驶过,仍然不为所动。
□美国《纽约时报》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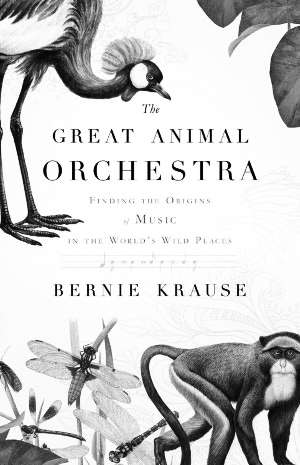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