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善的人们仍在为好莱坞“主旋律”欢呼
作者 [英] 加里·杨吉 译者 史春树
《
青年参考
》(
2015年02月04日
03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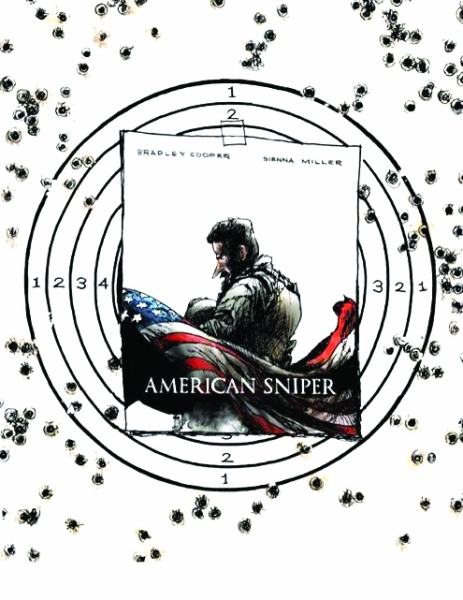 |
|
人权不是西方价值,而是普世价值。当你开始思考“哪些人的人权更值得保护,哪些人可以被暂时忽略”时,这种普世价值便岌岌可危了。
凡是看过新片《美国狙击手》的人,都会对它的直白印象深刻——这是一部讲述“杀人”的电影,没有道德说教,更没有关于杀戮是否正当的探讨。“我准备好了去见上帝,我对任何构成威胁的家伙都不会客气。”布拉德利·库珀饰演的克里斯·凯尔把伊拉克人称为“化外之民”,“在这个国家,我连一只苍蝇都不会放过。”
凯尔枪法神准,百步之外即可取人性命,更重要的是,他很喜欢军队交给自己的这份活计。“头一次击杀对手后,事情变得愈发简单,”他显然乐在其中,“我不用给自己打气,心理上没有任何负担,只需仔细寻找射程内的目标,待其进入瞄准器,就一枪送他回老家。”
不少人欣赏他这一套。迄今,《美国狙击手》已获6项奥斯卡奖提名,还创下了月度票房纪录。片中,当凯尔在1英里(1609米)外击毙叙利亚的“坏蛋”狙击手“穆斯塔法”时,我周围的观众欢声雷动。据说,该片在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尤其卖座,导演伊斯特伍德有望在英国、中国台湾、新西兰、秘鲁和意大利收获职业生涯中最绚丽的海外票房。
在保卫西方世界的大旗下,又一位英雄被好莱坞制造了出来。他的任务不是讽刺伊斯兰先知,而是对那些“为非作歹的野蛮人”实施肉体毁灭。根据阿(拉伯)裔美国人反歧视委员会的说法,该片上映以来,阿裔美国人和穆斯林遭遇的言语恐吓和人身威胁增加了3倍。其中原因,从凯尔的言论中不难窥见:“如果你发现16岁到65岁的男性,就让他们吃枪子儿。”这位狙击手如此描述自己的“交战守则”:“干掉所有男人,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凯尔,还有他的很多同路人,从不用别人看他的方式审视自身,通常也不会正眼看别人一下。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及其诱发的自恋情结,让他们以正义和道德的守护者自居。然而,在现实中,他们既不坚守正义,又不实践道德。他们这一类典型的西方人,心怀优越感又充满矛盾,屡屡做出令人反感的举动,却又弄不清楚自己为何招人讨厌。
“民族主义者,不仅不反对己方犯下的暴行,”如乔治·奥威尔所言,“而且对此充耳不闻……同样的行为是否应受谴责,说到底是根据政治偏好来决定的。”什么?本·拉登和萨达姆·侯赛因曾是西方的盟友?“没准是吧。但他们后来不又成了我们的敌人吗?重提这些陈年旧事不无聊吗?”我见过的很多人,都试图用类似的回答来蒙混过关。
正如美国一边要求古巴保护人权,一边在关塔那摩侵害这些权利那样,这是一种伪善。我们怎样看待这种伪善?特别是在那些本应被虔诚信守的原则受到公然蔑视的时候?
巴黎《查理周刊》血案发生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一次闭门会议上告诫道,必须使用武力对抗伊斯兰极端分子。美国国务卿克里则感慨道,这场惨祸是“一场更庞大的对抗,不仅是文明之间的,也是文明本身与那些反对文明的人之间的”。
那么,沙特阿拉伯呢?众所周知,它一直在为许多激进组织提供援助,更不是言论自由的粉丝。事实上,就在《查理周刊》遭袭两天后,沙特博主拉伊夫·巴达维被判处10年监禁和950次鞭刑(每周鞭笞50次),他的罪名就包括“侮辱伊斯兰教”。
只要“站队”正确,这些都无关紧要。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上周去世后,克里称赞他是“充满智慧与远见的人,美国失去了一位朋友,沙特、中东和世界失去了一位受人尊敬的领袖”。布莱尔也在社交媒体上不吝褒美:“阿卜杜拉深受国民爱戴,并且将被深深地怀念。”
人权不是西方价值,而是普世价值。当你开始思考“哪些人的人权更值得保护,哪些人可以被暂时忽略”时,这种普世价值便岌岌可危了。
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曾满怀忧虑地告诉我:“我最担心的是,大家慢慢都得了健忘症……我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守护那些即将被遗忘的,让人类保有良知的记忆。”
我追问,谁该对这样的集体健忘负责?对方解释道:“不是任何具体的个人,而是权力体制,这种体制总是以人类整体的名义,肆意决定谁值得被铭记、谁必须被遗忘……”
回到《美国狙击手》这部片子。入伍前,克里斯·凯尔只是出身于平民家庭的普通青年。看到自己认同的人们在世界的另一边被杀害,他决定去为他们复仇,却在战斗中逐渐迷失了方向。听起来熟悉吗?“我没有什么不满,”在意外被人枪杀前,他写道,“如果我必须对我的优先级排序,那就是上帝大于国家,国家大于家庭。”
凯尔本质上是个穿制服的圣战者,就像他的对头“穆斯塔法”是个着便装的士兵那样。
▋原载英国《卫报》,本文有删节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
人权不是西方价值,而是普世价值。当你开始思考“哪些人的人权更值得保护,哪些人可以被暂时忽略”时,这种普世价值便岌岌可危了。
凡是看过新片《美国狙击手》的人,都会对它的直白印象深刻——这是一部讲述“杀人”的电影,没有道德说教,更没有关于杀戮是否正当的探讨。“我准备好了去见上帝,我对任何构成威胁的家伙都不会客气。”布拉德利·库珀饰演的克里斯·凯尔把伊拉克人称为“化外之民”,“在这个国家,我连一只苍蝇都不会放过。”
凯尔枪法神准,百步之外即可取人性命,更重要的是,他很喜欢军队交给自己的这份活计。“头一次击杀对手后,事情变得愈发简单,”他显然乐在其中,“我不用给自己打气,心理上没有任何负担,只需仔细寻找射程内的目标,待其进入瞄准器,就一枪送他回老家。”
不少人欣赏他这一套。迄今,《美国狙击手》已获6项奥斯卡奖提名,还创下了月度票房纪录。片中,当凯尔在1英里(1609米)外击毙叙利亚的“坏蛋”狙击手“穆斯塔法”时,我周围的观众欢声雷动。据说,该片在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尤其卖座,导演伊斯特伍德有望在英国、中国台湾、新西兰、秘鲁和意大利收获职业生涯中最绚丽的海外票房。
在保卫西方世界的大旗下,又一位英雄被好莱坞制造了出来。他的任务不是讽刺伊斯兰先知,而是对那些“为非作歹的野蛮人”实施肉体毁灭。根据阿(拉伯)裔美国人反歧视委员会的说法,该片上映以来,阿裔美国人和穆斯林遭遇的言语恐吓和人身威胁增加了3倍。其中原因,从凯尔的言论中不难窥见:“如果你发现16岁到65岁的男性,就让他们吃枪子儿。”这位狙击手如此描述自己的“交战守则”:“干掉所有男人,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凯尔,还有他的很多同路人,从不用别人看他的方式审视自身,通常也不会正眼看别人一下。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及其诱发的自恋情结,让他们以正义和道德的守护者自居。然而,在现实中,他们既不坚守正义,又不实践道德。他们这一类典型的西方人,心怀优越感又充满矛盾,屡屡做出令人反感的举动,却又弄不清楚自己为何招人讨厌。
“民族主义者,不仅不反对己方犯下的暴行,”如乔治·奥威尔所言,“而且对此充耳不闻……同样的行为是否应受谴责,说到底是根据政治偏好来决定的。”什么?本·拉登和萨达姆·侯赛因曾是西方的盟友?“没准是吧。但他们后来不又成了我们的敌人吗?重提这些陈年旧事不无聊吗?”我见过的很多人,都试图用类似的回答来蒙混过关。
正如美国一边要求古巴保护人权,一边在关塔那摩侵害这些权利那样,这是一种伪善。我们怎样看待这种伪善?特别是在那些本应被虔诚信守的原则受到公然蔑视的时候?
巴黎《查理周刊》血案发生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一次闭门会议上告诫道,必须使用武力对抗伊斯兰极端分子。美国国务卿克里则感慨道,这场惨祸是“一场更庞大的对抗,不仅是文明之间的,也是文明本身与那些反对文明的人之间的”。
那么,沙特阿拉伯呢?众所周知,它一直在为许多激进组织提供援助,更不是言论自由的粉丝。事实上,就在《查理周刊》遭袭两天后,沙特博主拉伊夫·巴达维被判处10年监禁和950次鞭刑(每周鞭笞50次),他的罪名就包括“侮辱伊斯兰教”。
只要“站队”正确,这些都无关紧要。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上周去世后,克里称赞他是“充满智慧与远见的人,美国失去了一位朋友,沙特、中东和世界失去了一位受人尊敬的领袖”。布莱尔也在社交媒体上不吝褒美:“阿卜杜拉深受国民爱戴,并且将被深深地怀念。”
人权不是西方价值,而是普世价值。当你开始思考“哪些人的人权更值得保护,哪些人可以被暂时忽略”时,这种普世价值便岌岌可危了。
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曾满怀忧虑地告诉我:“我最担心的是,大家慢慢都得了健忘症……我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守护那些即将被遗忘的,让人类保有良知的记忆。”
我追问,谁该对这样的集体健忘负责?对方解释道:“不是任何具体的个人,而是权力体制,这种体制总是以人类整体的名义,肆意决定谁值得被铭记、谁必须被遗忘……”
回到《美国狙击手》这部片子。入伍前,克里斯·凯尔只是出身于平民家庭的普通青年。看到自己认同的人们在世界的另一边被杀害,他决定去为他们复仇,却在战斗中逐渐迷失了方向。听起来熟悉吗?“我没有什么不满,”在意外被人枪杀前,他写道,“如果我必须对我的优先级排序,那就是上帝大于国家,国家大于家庭。”
凯尔本质上是个穿制服的圣战者,就像他的对头“穆斯塔法”是个着便装的士兵那样。
▋原载英国《卫报》,本文有删节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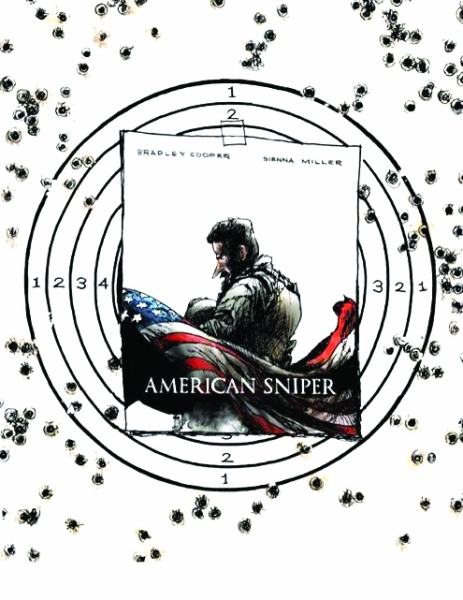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