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国门寻找爱(四)
背负沉重历史的德国人
本报特约撰稿 叶莹
《
青年参考
》(
2016年03月16日
10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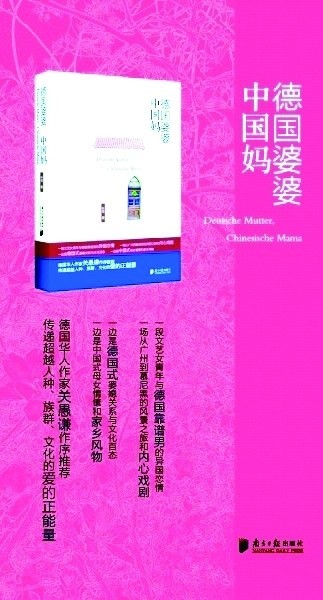 |
叶莹的长篇纪实小说《德国婆婆中国妈》 |
 |
德累斯顿城景 |
本版刊出的“走出国门寻找爱”系列文章在读者中颇受欢迎。经作者叶莹同意,本版从其长篇纪实小说《德国婆婆中国妈》中节选部分内容,分期连载,以飨读者。
一半移民组成的德国队捧起世界杯
人在德国,成为足球迷是很自然的,无论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
我也不例外。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我跟着大家一起为德国队疯狂。在南非世界杯快要揭开序幕之时,一只极没有体育道义的脚踢向了时任德国国家队队长巴拉克,他因此错过了南非赛事。没想到,2014年的世界杯赛场上,没有巴拉克的这支年轻队伍让整个世界震撼。
这支年轻的队伍是个多元文化的组合。23名队员里,11名队员有移民背景。德国如今是一个每5个人里就有1人有移民背景的国家,对法国等还在为移民融合问题头疼的欧洲国家而言,这支足球队有巨大的示范作用。
我不知道人们爱谈论的足球精神到底指的是什么,但对我这个居住在德国的外国人来说,足球精神也许就是能让我心甘情愿地去支持这支多元化的德国球队。
当然,足球体现的不只是体育精神,也是能带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还可以变成和政治紧密相关的难兄难弟。
在八强争霸战里,德国队要和英格兰队决一死战。同样是欧盟成员,但德国人知道,这个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兄弟,在过去60年里对德国是怎样的耿耿于怀。这场足球赛前,英格兰以壮烈的热情去支持自己的球队。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追踪这场赛事。
英格兰队自从1966年以那个“争议球”从对手德国手中抢走世界杯后,便与世界奖杯绝缘,这次也不例外。宿命也好,残酷也罢,这场比赛里裁判在关键比分上的一个误判,就决定了英格兰的士气不能再振。
很奇怪,赛后,那个误判球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而那场90分钟的精彩赛事中,德国队那近乎完美的团队配合却被人们淡忘。
在网上,我看到,支持英格兰队的一些球迷甚至狠狠地骂一声:“纳粹!”爱与恨的感情,是无法用尺子衡量的。有一刻,我深深地为德意志感到悲哀。二战后,德国对受害国该赔偿的款项都尽力赔偿,每年都有政要到纳粹集中营纪念地默哀致悔,几十年如一日,时刻提醒今日民众勿重蹈覆辙。如此诚恳地认错还是抹不掉邻国心里埋藏的深怨,一到关键时刻就会重揭伤疤。
弥漫在德国上空的二战阴影挥之不去
无论在战后重建中,踏实能干的德国人如何让自己的国家重新崛起为经济巨人,都不能让他们有扬眉吐气的自豪感。他们害怕别人提起“纳粹”,那是一页难以让人打开的历史,因为里面只有自己犯下的血淋淋的罪行。
对这段历史,德国人是如此敏感,如此不堪一击。几年前,一名电视台女主持人因为在自己的新书里说了一些希特勒的“好话”,称赞希特勒的家庭政策和修建高速公路的举措,马上被雇主解聘,所有媒体人都自觉地和她“划清界限”。
这其实是现代德国心态的真实写照。二战的阴影挥之不去,今日的德国人在缝隙里寻找有限的平衡。我开始有点明白,为什么我的丈夫爱德华从来不会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大大方方地来一句“我爱我的祖国,身为德国人很自豪”这样的话。
让这个国家更难释怀的,还有现在的欧元危机。
自从2009年年底,以标准普尔为首的三大美国评级公司突然宣布对希腊政府偿债能力降级,金融市场的信心立即受挫,仅占欧元区经济总量2.5%的希腊经济带领欧元一路探底。人们还没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喘过气来,就开始了新一轮恐慌。
德国是欧元区老大。劫富济贫、保持平稳向来是欧盟的精神主旨,别的国家出事了,谈起援助,德国首当其冲。无奈德国自身也痛,于是出现了关于救与不救的争论。
有偏激者提议,希腊把一些无人居住的小岛出卖抵债,引起希腊高层的阵阵愤慨。他们口口声声地抗议,说希腊经济如此萎靡不振是因为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抢走了希腊的财富。
以默克尔为首的德国政府,为了共同的欧洲、共同的欧元,倾囊而出。人们说,这个欧元援助计划不是北欧的国家援助南欧国家,而是穷人援助富人。因为援助的钱来自德国等国家人民的税款,却被用来挽救银行的倒闭,换句话说,是挽救银行各大股东。
南欧的民众不一定能从这些援助中得到实惠。钱虽然流出去了,但只要德国一请求南欧民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就会遭遇民众的怨愤,有人甚至给默克尔的画像画上希特勒的胡子、穿上纳粹的衣服。
看到这样的场面,我心里不由自主地偏向德国。当一个国家学会从罪恶中苏醒,竭尽全力去行善时,就会重获我的尊重。
德累斯顿:伤痕累累的美丽城市
暑假,我们带上婆婆一起到德国东部的老城德累斯顿游玩。我们是奔着德累斯顿那座重新修建了的巴洛克风格的圣母教堂来的。
“巴洛克”代表着一种艺术风格。这个词源于葡萄牙语“barroco”,意思是一种不规则的珍珠。它允许人们用无尽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去创造出一种优雅与浪漫共存的艺术。
说起德累斯顿,便会勾起婆婆对1945年那个情人节前夜的记忆。那天晚上,一排排飞机划破了埃尔福特市的夜空,向德累斯顿的方向飞去。战场上的夫君音信全无,她的心绪饱受折磨。听到这些轰鸣声,她彻夜难眠。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德累斯顿被空袭的消息传来。一个被誉为易北河的“佛罗伦萨”,有着美轮美奂的雄伟建筑及名画珍藏,为音乐家巴赫青睐不已的艺术城市,一夜之间几乎被英美联军的炸弹夷为平地。
那座圣母教堂未受到直接轰炸,但周围的火焰使得气温迅速升高,轰炸后的第二天,圣母教堂支撑不住了,终于也如小孩子搭建的积木般轰然倒地。
德累斯顿一直不是德国纳粹的重要城市,这里没有强大的军事防御,只有来自四方的许许多多的平民百姓。英美联军空袭之夜,苏联红军离德累斯顿只有50英里。不少人认为,如果从战略意义来说,这一空袭有“战争罪行”的嫌疑。
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德累斯顿受迫害的犹太人达万人之多,这是它受空袭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德国纳粹给世人带来的灾难太重,以至于德雷斯顿的平民只能深深压抑着家园尽毁的伤痛。
2005年,当德累斯顿圣母教堂的重建工程终于完成,重新以“世界上十大美丽建筑之一”呈现于世人面前时,婆婆对着电视机里的圣母教堂,激动得数次抹泪。
在普通德国人眼里,一座城市美丽与否不在于她是否拥有法兰克福式的现代金融中心大厦,而是人们是否能在她那里读到千百年的历史。历史是魂,现代是壳,德国人不愿意轻易让现代遮盖历史。
二战后,德累斯顿在东德统治下的45年里,因为经费等问题,老城中心一直保持着废墟的状态。德国统一后,开始了老城中心的重建工程。一个老城的重建就是要找回这座城市的魂,于是,从曾是萨克森王宫所在地的德累斯顿城堡到德国巴洛克国宝级建筑茨温格宫,都力求还原其真实的旧貌,包括那份历经岁月沧桑的黑砖灰石样。
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年轻一代,站在河岸边最美丽的“欧洲的阳台”——布吕尔平台上顾盼四周景观时,大概想象不出这是些不足20年的新建筑。
站在古老石拱桥上回望圣母教堂,顶上金色的十字饰物熠熠生辉,那是教堂落成时英国人专门制作出来赠送给圣母教堂的。旁边的一位长者也如我般痴痴地盯着河面上嬉戏的和平鸽。
她说,圣母教堂重新落成那年,她就随老伴从科隆搬到德累斯顿。她的老伴是德累斯顿人,城市被轰炸后,失去住所的他离开家乡,这一走就是半个多世纪。
她眉宇间露出淡淡的幽怨,说自己不喜欢这里,因为这里的亲戚在她的生日会上不会尽情欢笑,只会冷静礼节地干杯了事。她说,这里的人就是和家乡的人不一样。
我无语以对。作为一个旅游者,我深深地被这个城市的伤痛浸染。甚至有一刻我在想,如果让我在这里生活,我是否也会成为一个寡欢的人——即使这里有美丽的西斯廷圣母守候,我也抹不掉那份曾经沧海的落寞?
在德国,像婆婆那些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他们这辈子从没走出战争的阴影。战争总是政客打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旗号挑起的,最终的受害者还是国家和人民。
本文节选自叶莹长篇纪实小说《德国婆婆中国妈》,2015年5月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本版刊出的“走出国门寻找爱”系列文章在读者中颇受欢迎。经作者叶莹同意,本版从其长篇纪实小说《德国婆婆中国妈》中节选部分内容,分期连载,以飨读者。
一半移民组成的德国队捧起世界杯
人在德国,成为足球迷是很自然的,无论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
我也不例外。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我跟着大家一起为德国队疯狂。在南非世界杯快要揭开序幕之时,一只极没有体育道义的脚踢向了时任德国国家队队长巴拉克,他因此错过了南非赛事。没想到,2014年的世界杯赛场上,没有巴拉克的这支年轻队伍让整个世界震撼。
这支年轻的队伍是个多元文化的组合。23名队员里,11名队员有移民背景。德国如今是一个每5个人里就有1人有移民背景的国家,对法国等还在为移民融合问题头疼的欧洲国家而言,这支足球队有巨大的示范作用。
我不知道人们爱谈论的足球精神到底指的是什么,但对我这个居住在德国的外国人来说,足球精神也许就是能让我心甘情愿地去支持这支多元化的德国球队。
当然,足球体现的不只是体育精神,也是能带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还可以变成和政治紧密相关的难兄难弟。
在八强争霸战里,德国队要和英格兰队决一死战。同样是欧盟成员,但德国人知道,这个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兄弟,在过去60年里对德国是怎样的耿耿于怀。这场足球赛前,英格兰以壮烈的热情去支持自己的球队。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追踪这场赛事。
英格兰队自从1966年以那个“争议球”从对手德国手中抢走世界杯后,便与世界奖杯绝缘,这次也不例外。宿命也好,残酷也罢,这场比赛里裁判在关键比分上的一个误判,就决定了英格兰的士气不能再振。
很奇怪,赛后,那个误判球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而那场90分钟的精彩赛事中,德国队那近乎完美的团队配合却被人们淡忘。
在网上,我看到,支持英格兰队的一些球迷甚至狠狠地骂一声:“纳粹!”爱与恨的感情,是无法用尺子衡量的。有一刻,我深深地为德意志感到悲哀。二战后,德国对受害国该赔偿的款项都尽力赔偿,每年都有政要到纳粹集中营纪念地默哀致悔,几十年如一日,时刻提醒今日民众勿重蹈覆辙。如此诚恳地认错还是抹不掉邻国心里埋藏的深怨,一到关键时刻就会重揭伤疤。
弥漫在德国上空的二战阴影挥之不去
无论在战后重建中,踏实能干的德国人如何让自己的国家重新崛起为经济巨人,都不能让他们有扬眉吐气的自豪感。他们害怕别人提起“纳粹”,那是一页难以让人打开的历史,因为里面只有自己犯下的血淋淋的罪行。
对这段历史,德国人是如此敏感,如此不堪一击。几年前,一名电视台女主持人因为在自己的新书里说了一些希特勒的“好话”,称赞希特勒的家庭政策和修建高速公路的举措,马上被雇主解聘,所有媒体人都自觉地和她“划清界限”。
这其实是现代德国心态的真实写照。二战的阴影挥之不去,今日的德国人在缝隙里寻找有限的平衡。我开始有点明白,为什么我的丈夫爱德华从来不会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大大方方地来一句“我爱我的祖国,身为德国人很自豪”这样的话。
让这个国家更难释怀的,还有现在的欧元危机。
自从2009年年底,以标准普尔为首的三大美国评级公司突然宣布对希腊政府偿债能力降级,金融市场的信心立即受挫,仅占欧元区经济总量2.5%的希腊经济带领欧元一路探底。人们还没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喘过气来,就开始了新一轮恐慌。
德国是欧元区老大。劫富济贫、保持平稳向来是欧盟的精神主旨,别的国家出事了,谈起援助,德国首当其冲。无奈德国自身也痛,于是出现了关于救与不救的争论。
有偏激者提议,希腊把一些无人居住的小岛出卖抵债,引起希腊高层的阵阵愤慨。他们口口声声地抗议,说希腊经济如此萎靡不振是因为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抢走了希腊的财富。
以默克尔为首的德国政府,为了共同的欧洲、共同的欧元,倾囊而出。人们说,这个欧元援助计划不是北欧的国家援助南欧国家,而是穷人援助富人。因为援助的钱来自德国等国家人民的税款,却被用来挽救银行的倒闭,换句话说,是挽救银行各大股东。
南欧的民众不一定能从这些援助中得到实惠。钱虽然流出去了,但只要德国一请求南欧民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就会遭遇民众的怨愤,有人甚至给默克尔的画像画上希特勒的胡子、穿上纳粹的衣服。
看到这样的场面,我心里不由自主地偏向德国。当一个国家学会从罪恶中苏醒,竭尽全力去行善时,就会重获我的尊重。
德累斯顿:伤痕累累的美丽城市
暑假,我们带上婆婆一起到德国东部的老城德累斯顿游玩。我们是奔着德累斯顿那座重新修建了的巴洛克风格的圣母教堂来的。
“巴洛克”代表着一种艺术风格。这个词源于葡萄牙语“barroco”,意思是一种不规则的珍珠。它允许人们用无尽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去创造出一种优雅与浪漫共存的艺术。
说起德累斯顿,便会勾起婆婆对1945年那个情人节前夜的记忆。那天晚上,一排排飞机划破了埃尔福特市的夜空,向德累斯顿的方向飞去。战场上的夫君音信全无,她的心绪饱受折磨。听到这些轰鸣声,她彻夜难眠。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德累斯顿被空袭的消息传来。一个被誉为易北河的“佛罗伦萨”,有着美轮美奂的雄伟建筑及名画珍藏,为音乐家巴赫青睐不已的艺术城市,一夜之间几乎被英美联军的炸弹夷为平地。
那座圣母教堂未受到直接轰炸,但周围的火焰使得气温迅速升高,轰炸后的第二天,圣母教堂支撑不住了,终于也如小孩子搭建的积木般轰然倒地。
德累斯顿一直不是德国纳粹的重要城市,这里没有强大的军事防御,只有来自四方的许许多多的平民百姓。英美联军空袭之夜,苏联红军离德累斯顿只有50英里。不少人认为,如果从战略意义来说,这一空袭有“战争罪行”的嫌疑。
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德累斯顿受迫害的犹太人达万人之多,这是它受空袭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德国纳粹给世人带来的灾难太重,以至于德雷斯顿的平民只能深深压抑着家园尽毁的伤痛。
2005年,当德累斯顿圣母教堂的重建工程终于完成,重新以“世界上十大美丽建筑之一”呈现于世人面前时,婆婆对着电视机里的圣母教堂,激动得数次抹泪。
在普通德国人眼里,一座城市美丽与否不在于她是否拥有法兰克福式的现代金融中心大厦,而是人们是否能在她那里读到千百年的历史。历史是魂,现代是壳,德国人不愿意轻易让现代遮盖历史。
二战后,德累斯顿在东德统治下的45年里,因为经费等问题,老城中心一直保持着废墟的状态。德国统一后,开始了老城中心的重建工程。一个老城的重建就是要找回这座城市的魂,于是,从曾是萨克森王宫所在地的德累斯顿城堡到德国巴洛克国宝级建筑茨温格宫,都力求还原其真实的旧貌,包括那份历经岁月沧桑的黑砖灰石样。
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年轻一代,站在河岸边最美丽的“欧洲的阳台”——布吕尔平台上顾盼四周景观时,大概想象不出这是些不足20年的新建筑。
站在古老石拱桥上回望圣母教堂,顶上金色的十字饰物熠熠生辉,那是教堂落成时英国人专门制作出来赠送给圣母教堂的。旁边的一位长者也如我般痴痴地盯着河面上嬉戏的和平鸽。
她说,圣母教堂重新落成那年,她就随老伴从科隆搬到德累斯顿。她的老伴是德累斯顿人,城市被轰炸后,失去住所的他离开家乡,这一走就是半个多世纪。
她眉宇间露出淡淡的幽怨,说自己不喜欢这里,因为这里的亲戚在她的生日会上不会尽情欢笑,只会冷静礼节地干杯了事。她说,这里的人就是和家乡的人不一样。
我无语以对。作为一个旅游者,我深深地被这个城市的伤痛浸染。甚至有一刻我在想,如果让我在这里生活,我是否也会成为一个寡欢的人——即使这里有美丽的西斯廷圣母守候,我也抹不掉那份曾经沧海的落寞?
在德国,像婆婆那些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他们这辈子从没走出战争的阴影。战争总是政客打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旗号挑起的,最终的受害者还是国家和人民。
本文节选自叶莹长篇纪实小说《德国婆婆中国妈》,2015年5月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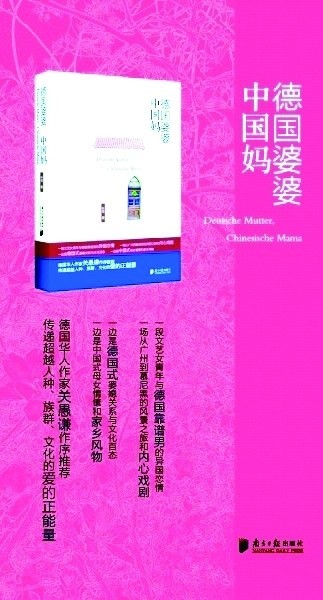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