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国门寻找爱(三)
德国埃尔福特市的中国媳妇
本报特约撰稿 叶莹
《
青年参考
》(
2015年12月23日
10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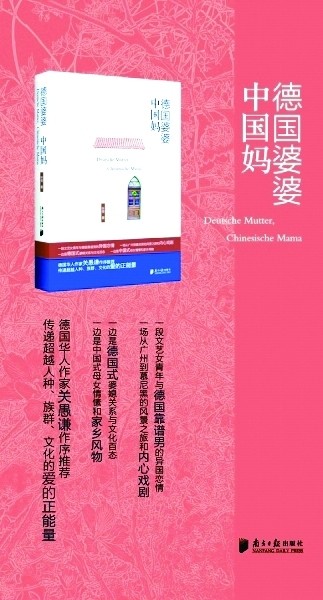 |
叶莹的长篇纪实小说《德国婆婆中国妈》。 |
 |
作者和丈夫的结婚照。 |
【本版刊出的“走出国门寻找爱”系列文章在读者中颇受欢迎。经作者叶莹同意,本版从其长篇纪实小说《德国婆婆中国妈》中节选作者远嫁德国后的内容,分期连载,以飨读者。】
令我难忘的德国婚礼
我和爱德华的婚礼定在金秋10月的一个周六在德国埃尔福特市举行。
婚礼上,舞会的帷幕拉开。爱德华脱下西服外套,里面穿的是丝绸质地的灰底暗花小马甲配白衬衣。他拥我入怀,我们在房间的中心旋转起轻快的舞步。我的旗袍摩擦着他的小马甲,丝绸与丝绸的相碰突然有了电光火花的热度,舞曲的旋律越来越急促,我忘乎所以地放任自己晕眩的感觉,任由他带着我旋转起来。
父母缺席的婚礼,让我的心一直隐隐作疼。从此以后,我便要做一个远离父母的异乡人了。我的丈夫,爱德华,他拥有我少女时梦寐以求的一切优点:温文尔雅,乐观耿直,孝顺,有爱心。
当他站在我面前时,我测量不到心跳加速的频率,可我还是那么心甘情愿,任由他握紧我的双手。他就要成为我的新生活,我没有害怕。可我不知道我们面对的将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是否会如愿有两三个孩子?我们是否会遵守对我母亲的诺言,经常回去看她?我们是否真能做到主婚人所说的那样,这一生,无论是在人生高峰还是低谷,都携手同进退,直到……
我的头突然被自己的思想炸疼了。我随着音乐旋转的力气越来越微弱,最后有如一只患了哮喘的小鼠,搭在爱德华的臂弯上,等待着音乐的终止。
爱德华的父亲——从今以后是我的公公了,他满脸红光,不时用纸巾擦额头上渗出的微汗。
他愉快地和停留在他面前的每位客人畅谈,而几乎每一个和他畅谈过的客人都会走过来对我笑语一句:“你的公公总是问我,站在爱德华旁边的那个漂亮女孩是谁啊?”
我远远看着不停擦汗的公公,就像听了一则幽默的故事般,和众人狂笑一通。虽然这并不是值得笑的事情——他的健忘症,似乎在我们的疏忽中更上一层楼了?
我把目光投向爱德华的母亲,我的婆婆。她和不同的舞伴跳完一曲又一曲。我为她依然灵动的舞姿着迷。
子夜时分的钟声敲响,我们的宴会跨进另一个神圣的时刻——爱德华的父母迎来了他们的六十周年钻石婚。六十周年相濡以沫的日子,有幸分享他们的幸福,对我和爱德华这对新人来说,也是缘分吧。
第二天,埃尔福特市的副市长和他的助手拎着一篮水果,亲自上门祝贺公公婆婆的钻石婚庆,还带来了市长亲笔签字的贺信。副市长对着他们一个劲儿地感慨:“你们一点都不像八十多岁的人,一点都不显老呀! ”公公笑呵呵地回答:“是呀,活在美丽的埃尔福特,舍不得老呀!”
道别时,副市长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对我爽朗一笑:“德国欢迎你啊,埃尔福特欢迎你啊,中国媳妇!”
家庭与事业——女人的烦恼
婚后,我渐渐收回放纵的心情。每天送爱德华上班后,我便努力投简历找工作。因为我的德语还不是非常好,所以选择大受限制。我集中精力找一些和中国有业务的公司。自己在网上搜索了一阵子后,打了很多电话,碰了满鼻子的灰。写了无数简历,收到礼貌的拒绝信也无数。
不久,我接到了一家公司的面试通知。面试时,我和两位面试官用德语交谈了半个多小时。他们夸我德语好,说就凭这点,他们相信我是一个学习新事物很容易上手的人。我心中充满了希望。
突然,其中一位面试官问我:“你会很快考虑要孩子吗?如果派你到中国两年再回来,你能做到吗?”他提的这个问题令我措手不及。面试在最后的客套中草草结束。
晚上爱德华回家,我跟他讲了面试的情况。我告诉他那家公司提的那些问题,对一个女人来说太伤人了。爱德华也很愤愤不平,说这样的问题是很私人的,是不允许随便问的。
“不允许问”和“不想问”是两码事。如果这位经理不是如此直截了当,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发问,譬如“我们这个职位需要怎样条件的人,做怎样的工作,你觉得你能胜任吗”,我会更释然。
几天后我便收到公司的拒绝函,这于我完全是意料中事。只是我更真实地体会到,自己在德国的职场生活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灰色的。
后来,我得到了一份为期半年的临时工作,在一个展览公司里协助做些零碎的项目管理工作。
曼是我的上司,年龄和我相仿。一天,市政府经济部有一个活动,是接待来自中国的一个招商代表团,曼把我也带上了。我没想到,这个代表团竟然来自广州。
他们向在场的听众描述了广州的发展宏图:南沙的开发、大学城的兴建、科学城的规划、留学人员创业园等项目,言辞里透露出求贤若渴、求资若饥的迫切。
这是一个让我心情无法平静的招商会,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有一次父亲和我在电话里说起番禺的大学城开发时,曾感慨地叹了一口气:你要是在德国读完书后,能回大学城当老师,该多好!
回来的路上,曼仰起她那张俏脸对我说:“你的家乡真美啊!依山傍水,现代繁华。”
曼告诉我,她的男朋友要被派到中国去两年。我有些羡慕地对她说:那你一定要在他去中国之前和他结婚,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和他去中国了。
“可是,我要放弃这里的工作。两年后我回来了,没有工作怎么办?重新找一份像现在这么好的工作,并不容易。”她设计的理想生活,依然是世界为她转动。
“两年后,或许你们有了孩子,你便要在家待着啦。”我提醒她。
“哎呀,你别说了,他那点工资肯定大半都要给他前妻,怎么能养我和孩子呢?我肯定要工作的。”
我被她的话弄得有点晕了,心里想,女人啊女人,又要情又要事业,有时候就是这般难。我以为我这个外国人在德国要两全其美很难,没想到事业上风生水起的德国女人也会有难题。
好像只要身为女人,便逃不掉家庭和事业难两全的烦恼。
婆婆和我“明明白白”地算账
我和爱德华婚后半年,春天里,婆婆因为一个小手术需要住院一个多星期,她问我们可不可以把公公接到慕尼黑。周末,我们动身回埃尔福特。
婆婆一看见我们,满脸写着内疚,不停地说:“真是对不起,要麻烦你们了。白天爱德华上班,便是你一个人和阿爸在一起啦。”
我其实一点不觉得公公会是负担,他能吃能走,只不过有点健忘而已。和他在一起,听他唱唱老歌,说说古诗,总比一个人闷在家里为找工作而烦恼好。
一天上午,在林中陪公公漫步的我,被林子深处的一大片紫色小野花吸引。我正想蹲下来,公公却一把拉过我,摇头晃脑地念了一堆韵律有致的句子。我听了个大概,觉得是关于树林和野花的描述。我以为他也在惊叹这些出污泥而不染的小野花,便欲转身蹲下来折花。阿爸这一次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别别,别把花来折。难道你忍心看我烟花寂落芳华尽?”
我好奇地问:“阿爸,你怎么不做个诗人呢?你说话太有诗意了。”
“我给你念的就是诗歌啊!最后一段是我根据歌德的诗改写的。”
“是吗!那你一句一句教我,我想把这首诗背下来。”我兴致勃勃地央求他。和一个健忘的老人在一起,如果想不觉得无聊,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双方都有兴趣的话题。我决定让阿爸把对诗歌的嗜好转化为对我的文学陶冶。
“当然可以,我的小姑娘!”他眼中的我,永远是“孙女”级别的小。我享受这种感觉。
婆婆的手术进展顺利,一个星期后,她出院回家了。等我们把公公送回去的时候,她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见到我时,婆婆把我拉进她的卧房,摊开右手,里面躺着几张钞票。她把钱塞进我手里,用近乎命令的声调说:“请你收下!一定收下!这些天照顾阿爸辛苦了,太难为你了。你就用这点钱给自己买件漂亮衣服啊或者鞋子什么的,让自己高兴一下啊!”
我喉咙里像有只苍蝇似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觉得心里有一股悲哀。她,我的婆婆,看来是会永远和我“明明白白”地算账的。我照顾公公是天经地义的一件小事,可是在她眼里,我却是要得到报酬的“劳工”。
【本版刊出的“走出国门寻找爱”系列文章在读者中颇受欢迎。经作者叶莹同意,本版从其长篇纪实小说《德国婆婆中国妈》中节选作者远嫁德国后的内容,分期连载,以飨读者。】
令我难忘的德国婚礼
我和爱德华的婚礼定在金秋10月的一个周六在德国埃尔福特市举行。
婚礼上,舞会的帷幕拉开。爱德华脱下西服外套,里面穿的是丝绸质地的灰底暗花小马甲配白衬衣。他拥我入怀,我们在房间的中心旋转起轻快的舞步。我的旗袍摩擦着他的小马甲,丝绸与丝绸的相碰突然有了电光火花的热度,舞曲的旋律越来越急促,我忘乎所以地放任自己晕眩的感觉,任由他带着我旋转起来。
父母缺席的婚礼,让我的心一直隐隐作疼。从此以后,我便要做一个远离父母的异乡人了。我的丈夫,爱德华,他拥有我少女时梦寐以求的一切优点:温文尔雅,乐观耿直,孝顺,有爱心。
当他站在我面前时,我测量不到心跳加速的频率,可我还是那么心甘情愿,任由他握紧我的双手。他就要成为我的新生活,我没有害怕。可我不知道我们面对的将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是否会如愿有两三个孩子?我们是否会遵守对我母亲的诺言,经常回去看她?我们是否真能做到主婚人所说的那样,这一生,无论是在人生高峰还是低谷,都携手同进退,直到……
我的头突然被自己的思想炸疼了。我随着音乐旋转的力气越来越微弱,最后有如一只患了哮喘的小鼠,搭在爱德华的臂弯上,等待着音乐的终止。
爱德华的父亲——从今以后是我的公公了,他满脸红光,不时用纸巾擦额头上渗出的微汗。
他愉快地和停留在他面前的每位客人畅谈,而几乎每一个和他畅谈过的客人都会走过来对我笑语一句:“你的公公总是问我,站在爱德华旁边的那个漂亮女孩是谁啊?”
我远远看着不停擦汗的公公,就像听了一则幽默的故事般,和众人狂笑一通。虽然这并不是值得笑的事情——他的健忘症,似乎在我们的疏忽中更上一层楼了?
我把目光投向爱德华的母亲,我的婆婆。她和不同的舞伴跳完一曲又一曲。我为她依然灵动的舞姿着迷。
子夜时分的钟声敲响,我们的宴会跨进另一个神圣的时刻——爱德华的父母迎来了他们的六十周年钻石婚。六十周年相濡以沫的日子,有幸分享他们的幸福,对我和爱德华这对新人来说,也是缘分吧。
第二天,埃尔福特市的副市长和他的助手拎着一篮水果,亲自上门祝贺公公婆婆的钻石婚庆,还带来了市长亲笔签字的贺信。副市长对着他们一个劲儿地感慨:“你们一点都不像八十多岁的人,一点都不显老呀! ”公公笑呵呵地回答:“是呀,活在美丽的埃尔福特,舍不得老呀!”
道别时,副市长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对我爽朗一笑:“德国欢迎你啊,埃尔福特欢迎你啊,中国媳妇!”
家庭与事业——女人的烦恼
婚后,我渐渐收回放纵的心情。每天送爱德华上班后,我便努力投简历找工作。因为我的德语还不是非常好,所以选择大受限制。我集中精力找一些和中国有业务的公司。自己在网上搜索了一阵子后,打了很多电话,碰了满鼻子的灰。写了无数简历,收到礼貌的拒绝信也无数。
不久,我接到了一家公司的面试通知。面试时,我和两位面试官用德语交谈了半个多小时。他们夸我德语好,说就凭这点,他们相信我是一个学习新事物很容易上手的人。我心中充满了希望。
突然,其中一位面试官问我:“你会很快考虑要孩子吗?如果派你到中国两年再回来,你能做到吗?”他提的这个问题令我措手不及。面试在最后的客套中草草结束。
晚上爱德华回家,我跟他讲了面试的情况。我告诉他那家公司提的那些问题,对一个女人来说太伤人了。爱德华也很愤愤不平,说这样的问题是很私人的,是不允许随便问的。
“不允许问”和“不想问”是两码事。如果这位经理不是如此直截了当,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发问,譬如“我们这个职位需要怎样条件的人,做怎样的工作,你觉得你能胜任吗”,我会更释然。
几天后我便收到公司的拒绝函,这于我完全是意料中事。只是我更真实地体会到,自己在德国的职场生活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灰色的。
后来,我得到了一份为期半年的临时工作,在一个展览公司里协助做些零碎的项目管理工作。
曼是我的上司,年龄和我相仿。一天,市政府经济部有一个活动,是接待来自中国的一个招商代表团,曼把我也带上了。我没想到,这个代表团竟然来自广州。
他们向在场的听众描述了广州的发展宏图:南沙的开发、大学城的兴建、科学城的规划、留学人员创业园等项目,言辞里透露出求贤若渴、求资若饥的迫切。
这是一个让我心情无法平静的招商会,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有一次父亲和我在电话里说起番禺的大学城开发时,曾感慨地叹了一口气:你要是在德国读完书后,能回大学城当老师,该多好!
回来的路上,曼仰起她那张俏脸对我说:“你的家乡真美啊!依山傍水,现代繁华。”
曼告诉我,她的男朋友要被派到中国去两年。我有些羡慕地对她说:那你一定要在他去中国之前和他结婚,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和他去中国了。
“可是,我要放弃这里的工作。两年后我回来了,没有工作怎么办?重新找一份像现在这么好的工作,并不容易。”她设计的理想生活,依然是世界为她转动。
“两年后,或许你们有了孩子,你便要在家待着啦。”我提醒她。
“哎呀,你别说了,他那点工资肯定大半都要给他前妻,怎么能养我和孩子呢?我肯定要工作的。”
我被她的话弄得有点晕了,心里想,女人啊女人,又要情又要事业,有时候就是这般难。我以为我这个外国人在德国要两全其美很难,没想到事业上风生水起的德国女人也会有难题。
好像只要身为女人,便逃不掉家庭和事业难两全的烦恼。
婆婆和我“明明白白”地算账
我和爱德华婚后半年,春天里,婆婆因为一个小手术需要住院一个多星期,她问我们可不可以把公公接到慕尼黑。周末,我们动身回埃尔福特。
婆婆一看见我们,满脸写着内疚,不停地说:“真是对不起,要麻烦你们了。白天爱德华上班,便是你一个人和阿爸在一起啦。”
我其实一点不觉得公公会是负担,他能吃能走,只不过有点健忘而已。和他在一起,听他唱唱老歌,说说古诗,总比一个人闷在家里为找工作而烦恼好。
一天上午,在林中陪公公漫步的我,被林子深处的一大片紫色小野花吸引。我正想蹲下来,公公却一把拉过我,摇头晃脑地念了一堆韵律有致的句子。我听了个大概,觉得是关于树林和野花的描述。我以为他也在惊叹这些出污泥而不染的小野花,便欲转身蹲下来折花。阿爸这一次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别别,别把花来折。难道你忍心看我烟花寂落芳华尽?”
我好奇地问:“阿爸,你怎么不做个诗人呢?你说话太有诗意了。”
“我给你念的就是诗歌啊!最后一段是我根据歌德的诗改写的。”
“是吗!那你一句一句教我,我想把这首诗背下来。”我兴致勃勃地央求他。和一个健忘的老人在一起,如果想不觉得无聊,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双方都有兴趣的话题。我决定让阿爸把对诗歌的嗜好转化为对我的文学陶冶。
“当然可以,我的小姑娘!”他眼中的我,永远是“孙女”级别的小。我享受这种感觉。
婆婆的手术进展顺利,一个星期后,她出院回家了。等我们把公公送回去的时候,她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见到我时,婆婆把我拉进她的卧房,摊开右手,里面躺着几张钞票。她把钱塞进我手里,用近乎命令的声调说:“请你收下!一定收下!这些天照顾阿爸辛苦了,太难为你了。你就用这点钱给自己买件漂亮衣服啊或者鞋子什么的,让自己高兴一下啊!”
我喉咙里像有只苍蝇似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觉得心里有一股悲哀。她,我的婆婆,看来是会永远和我“明明白白”地算账的。我照顾公公是天经地义的一件小事,可是在她眼里,我却是要得到报酬的“劳工”。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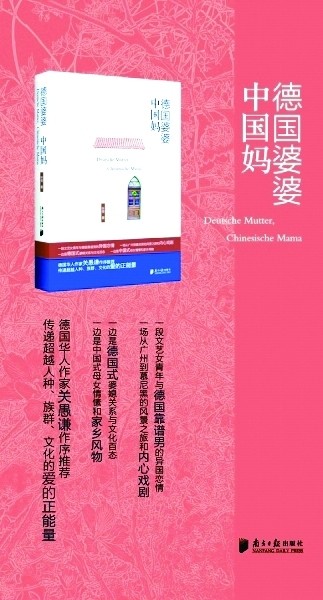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