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世界里的伦敦雾霾
作者 [美]迈克尔·德瑞塔 译者 韦盖利
《
青年参考
》(
2015年12月09日
20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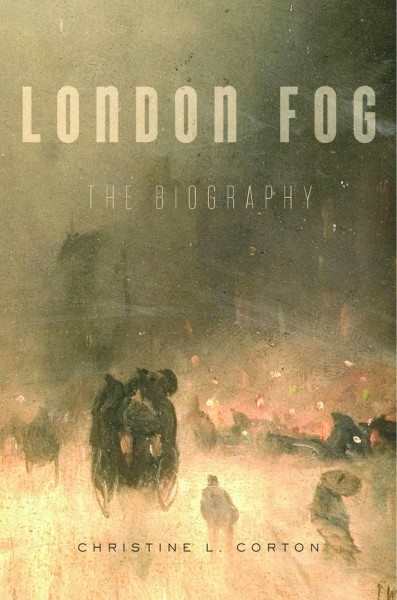 |
《伦敦之雾:传记》(London Fog: The Biography),(美国)贝尔纳普出版社2015年11月。 |
百年前,弥漫于英国首都的雾霾在酿成公共卫生灾难的同时,也激发了文艺人士的创作灵感,并借助后者的妙笔名篇,重塑了伦敦在现实世界中的形象。
19世纪八九十年代,伦敦的空气质量跌至历史最低点,每年11月到12月,这座城市都会在浓重的雾霾中“隐身”一段时间。事实上,1853年,查尔斯·狄更斯在其《荒凉山庄》的开篇,就把伦敦的雾描述为,“烟雾从烟囱管帽降下,形成浅黑色的毛毛雨,中间带着煤灰烟尘,像成形的雪花那么大……让人觉得太阳已经死去。”他说,伦敦当时的雾,不是那种“柔软的、鸽子灰色”的雾,而是散发着恶臭,呈黄色或黑色,几乎让人窒息。
英国学者克里斯汀·L·哥顿在新著《伦敦之雾:传记》里提醒读者,雾霾曾被视为英国首都的一部分。早在17世纪,日记写手约翰·伊夫琳就开始抱怨四面八方的石灰窑污染了空气。到维多利亚女王1837年登基时,浓雾已经影响到市民日常出行,无论乘马车还是行走都变得困难——连续很多天能见度过低。1892年的一份统计显示,从1886年到1890年,伦敦平均每年有63天是大雾天气。在昏黄的街头,“linklighters”,即提着自制手电筒的流浪儿提供有偿带路服务;有时,不幸的有钱人会被诱骗到深巷里,惨遭抢劫。
除了劣质家用暖炉,伦敦的雾霾大部分是变本加厉的工业活动贡献的。空气中无处不在的硫元素,使它看起来像“一碗豌豆汤”(用捣裂的干豌豆煮成,不用新鲜豌豆)。结果,不知从何时起,伦敦的浓雾便得了个“豌豆汤”的绰号,后来更被戏谑地称为“伦敦特供”。
这是一场公共卫生领域的灾难。人们惊恐地发现,马戏团的公牛呼吸困难,倒地身亡。空气里的污物无情地冲击着口鼻,公共马车夫要靠喝威士忌来清喉。满是泥尘的空气还会渗入门缝、窗缝,给家具蒙上油腻的、有些像煤尘的灰土。许多植物也枯萎了,如哥顿指出,悬铃树之所以成为伦敦的主力绿化树种,是因为它们光滑的叶子不易吸附污物。
进入20世纪,英国政府开始着手治理污染物排放,但不难想见,工厂老板们不愿意进行技术改革,因为那样要花钱。直到50年代中期,当局才有足够有效的法律手段来制止对大气的超标排放,减少“雾王”出现的次数。如今,伦敦的雾中基本只剩下水蒸气了。
值得一提的是,哥顿的《伦敦之雾》独辟蹊径,系统地跟踪了雾霾这种现象在艺术和文学中的表现形式。相关章节充满了报纸插图、惠斯勒和莫奈等人的印象主义画作的复制品,还附加了很多照片,甚至有《开膛手杰克》和《福尔摩斯》等电影的剧照。
总体来说,她追溯了英国文学对雾的隐喻性用法,颇具见地的指出:对很多作家来说,雾“成了一种消除社会秩序的分层体系的象征,它模糊了道德界限、用朦胧和怀疑来代替确认和肯定”。在一部接一部的文学作品中,雾引起“社会危机、不道德、犯罪和无序”,在黑暗中,礼崩乐坏,小偷和杀人犯作案后会轻易逃脱惩罚,甚至完全消失无踪。
而在早期的科幻小说中,浓雾俨然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廉·迪莱尔·哈伊在1880年出版的《杰出城市的厄运》中,精准地预见了有毒的空气令大批市民窒息而死的惨况。在1882年出版的短篇《伦敦的厄运》里,罗伯特·巴尔形象地将致命的大雾比喻成“一张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空气垫子,向整个城市压下来”。休·欧文1908年推出的《毒云》里,伦敦人被一种类似芥子气的外来物质消灭。这些启示录式的、富有末世特征的狂野想象,在1901年出版的《紫云》中达到最高点,在该书中,被毒雾毁掉的不仅是伦敦,还有全世界。
哥顿还讨论了“关于伦敦大雾的、最伟大的书”——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变身怪医》(1886)。在那部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典里,浓雾起的是“棺材罩”的作用,掩盖了一桩谋杀案的真相。与此相对照,莫利·罗伯茨的《雾》重点刻画了一个盲人乞丐的道德优越感,他的工作就是引导“上等人”穿过陷入黑暗、并且充斥着暴力的伦敦城区。
更好玩的是,法国作家J·K·于斯曼在其《违背自然》中塑造的主角之一,曾利用巴黎有雾的日子假装自己在伦敦,既省下了旅行成本,又不用受舟车劳顿之苦。王尔德作为于斯曼的追随者,坚持认为作家和画家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英国首都的气候特征,“人们看到雾,不止是因为有雾,而是因为诗人和画家们教会了他们雾的效果的神秘魅力。”
如今,伦敦的空气已恢复清新。曾令人胆寒的浓雾更多地被视作维多利亚时代鬼故事乃至福尔摩斯探案的背景。“那是9月的一个傍晚,还没到7点,但整天都是阴天,密密的、毛毛雨似的雾向城市笼罩下来。”大侦探的助手华生在《四签名》中叹道。时隔百年,每逢秋日傍晚,这段文字读起来仍令人神往;显然,如果没有雾,这个故事的趣味性必定要打折。
美国《华盛顿邮报》
百年前,弥漫于英国首都的雾霾在酿成公共卫生灾难的同时,也激发了文艺人士的创作灵感,并借助后者的妙笔名篇,重塑了伦敦在现实世界中的形象。
19世纪八九十年代,伦敦的空气质量跌至历史最低点,每年11月到12月,这座城市都会在浓重的雾霾中“隐身”一段时间。事实上,1853年,查尔斯·狄更斯在其《荒凉山庄》的开篇,就把伦敦的雾描述为,“烟雾从烟囱管帽降下,形成浅黑色的毛毛雨,中间带着煤灰烟尘,像成形的雪花那么大……让人觉得太阳已经死去。”他说,伦敦当时的雾,不是那种“柔软的、鸽子灰色”的雾,而是散发着恶臭,呈黄色或黑色,几乎让人窒息。
英国学者克里斯汀·L·哥顿在新著《伦敦之雾:传记》里提醒读者,雾霾曾被视为英国首都的一部分。早在17世纪,日记写手约翰·伊夫琳就开始抱怨四面八方的石灰窑污染了空气。到维多利亚女王1837年登基时,浓雾已经影响到市民日常出行,无论乘马车还是行走都变得困难——连续很多天能见度过低。1892年的一份统计显示,从1886年到1890年,伦敦平均每年有63天是大雾天气。在昏黄的街头,“linklighters”,即提着自制手电筒的流浪儿提供有偿带路服务;有时,不幸的有钱人会被诱骗到深巷里,惨遭抢劫。
除了劣质家用暖炉,伦敦的雾霾大部分是变本加厉的工业活动贡献的。空气中无处不在的硫元素,使它看起来像“一碗豌豆汤”(用捣裂的干豌豆煮成,不用新鲜豌豆)。结果,不知从何时起,伦敦的浓雾便得了个“豌豆汤”的绰号,后来更被戏谑地称为“伦敦特供”。
这是一场公共卫生领域的灾难。人们惊恐地发现,马戏团的公牛呼吸困难,倒地身亡。空气里的污物无情地冲击着口鼻,公共马车夫要靠喝威士忌来清喉。满是泥尘的空气还会渗入门缝、窗缝,给家具蒙上油腻的、有些像煤尘的灰土。许多植物也枯萎了,如哥顿指出,悬铃树之所以成为伦敦的主力绿化树种,是因为它们光滑的叶子不易吸附污物。
进入20世纪,英国政府开始着手治理污染物排放,但不难想见,工厂老板们不愿意进行技术改革,因为那样要花钱。直到50年代中期,当局才有足够有效的法律手段来制止对大气的超标排放,减少“雾王”出现的次数。如今,伦敦的雾中基本只剩下水蒸气了。
值得一提的是,哥顿的《伦敦之雾》独辟蹊径,系统地跟踪了雾霾这种现象在艺术和文学中的表现形式。相关章节充满了报纸插图、惠斯勒和莫奈等人的印象主义画作的复制品,还附加了很多照片,甚至有《开膛手杰克》和《福尔摩斯》等电影的剧照。
总体来说,她追溯了英国文学对雾的隐喻性用法,颇具见地的指出:对很多作家来说,雾“成了一种消除社会秩序的分层体系的象征,它模糊了道德界限、用朦胧和怀疑来代替确认和肯定”。在一部接一部的文学作品中,雾引起“社会危机、不道德、犯罪和无序”,在黑暗中,礼崩乐坏,小偷和杀人犯作案后会轻易逃脱惩罚,甚至完全消失无踪。
而在早期的科幻小说中,浓雾俨然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廉·迪莱尔·哈伊在1880年出版的《杰出城市的厄运》中,精准地预见了有毒的空气令大批市民窒息而死的惨况。在1882年出版的短篇《伦敦的厄运》里,罗伯特·巴尔形象地将致命的大雾比喻成“一张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空气垫子,向整个城市压下来”。休·欧文1908年推出的《毒云》里,伦敦人被一种类似芥子气的外来物质消灭。这些启示录式的、富有末世特征的狂野想象,在1901年出版的《紫云》中达到最高点,在该书中,被毒雾毁掉的不仅是伦敦,还有全世界。
哥顿还讨论了“关于伦敦大雾的、最伟大的书”——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变身怪医》(1886)。在那部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典里,浓雾起的是“棺材罩”的作用,掩盖了一桩谋杀案的真相。与此相对照,莫利·罗伯茨的《雾》重点刻画了一个盲人乞丐的道德优越感,他的工作就是引导“上等人”穿过陷入黑暗、并且充斥着暴力的伦敦城区。
更好玩的是,法国作家J·K·于斯曼在其《违背自然》中塑造的主角之一,曾利用巴黎有雾的日子假装自己在伦敦,既省下了旅行成本,又不用受舟车劳顿之苦。王尔德作为于斯曼的追随者,坚持认为作家和画家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英国首都的气候特征,“人们看到雾,不止是因为有雾,而是因为诗人和画家们教会了他们雾的效果的神秘魅力。”
如今,伦敦的空气已恢复清新。曾令人胆寒的浓雾更多地被视作维多利亚时代鬼故事乃至福尔摩斯探案的背景。“那是9月的一个傍晚,还没到7点,但整天都是阴天,密密的、毛毛雨似的雾向城市笼罩下来。”大侦探的助手华生在《四签名》中叹道。时隔百年,每逢秋日傍晚,这段文字读起来仍令人神往;显然,如果没有雾,这个故事的趣味性必定要打折。
美国《华盛顿邮报》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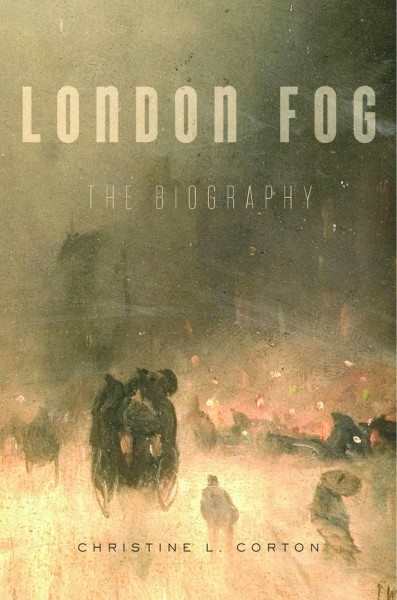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