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欧美反恐斗争是如何跑偏的
[英] 罗宾·雅辛-卡萨伯 译者 韦盖利
《
青年参考
》(
2014年05月28日
32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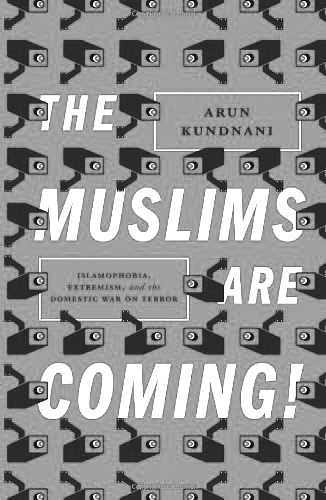 |
《穆斯林来了!》(The Muslims Are Coming!),左页出版社2014年3月,256页。 |
本书作者主张,恐怖主义的根源在社会政策而非思想文化领域。欧美诸国对穆斯林群体特定意识形态的过度警惕和防范,只会加深隔阂,而对减少暴力无益。
比起陈词滥调的“反恐战争”之类说法,亚兰·康德纳尼聚焦恐怖主义和西方国家的反恐行动时,在遣词造句上显得更具智慧。他在新著《穆斯林来了!》的开篇写道,“恐怖主义并非极端政治的产物,而是‘政治不举’的症状。”所以,解药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强大、积极和自信的穆斯林团体,外加充分的公民权利。”但在现实中的大西洋两岸,穆斯林的意见往往被犯罪化,言论也遭到压制。如此粗鲁的方式极有可能导致暴力增多,而非减少。
在康德纳尼笔下,英美等国针对穆斯林的两种主要的防御措施——“文化主义”和“改革主义”,注重的是目标人群的意识形态,而非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说起文化主义,其头号吹鼓手当属伯纳德·路易斯,这位深受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宠信的历史学家,将问题归结于伊斯兰教本身,称“伊斯兰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同崇尚民主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基于相似的思维,另一位共和党人米特·罗姆尼如此解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分岐:“文化造成了所有不同”——换言之,数十年的占领、隔离和战争根本无所谓。
而在欧洲,作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相信,2005年巴黎郊区居民骚乱,只是因为他们是穆斯林,而与失业率高、住房条件差和警察滥权无关。或许是最荒唐的论调出自马汀·埃米斯的小品文《第二架飞机》,在文中,埃米斯轻松地承认自己一点也不懂地缘政治,但宣称自己很懂“男人”——“9·11”事件不是因为政治,而是因为涉事的穆斯林深受“性挫折”。类似的论述古已有之。笔者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的肯尼亚,就有所谓心理学家宣称,当地人的反殖民起义“并非政治因素引起,应当从精神病学方面找原因”。
至于改革主义,它的问题在于对伊斯兰文化的随意解读。作为表征,2009年,奥巴马在开罗演讲时提到,“有节制”的穆斯林文化有助于解决政治冲突。自称熟读古兰经的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则认为,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是“对伊斯兰教条的狂热迷恋”。
对穆斯林群体思想动态的关注,往往意味着国家深度介入后者的生活,以“改善信仰”。虽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有待进一步分析,穆斯林还是被笼统地分为“极端主义者”和“有节制者”。对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强调,还催生了一类所谓“美化恐怖主义罪”。随着思想文化领域成为战场,西方国家把相对新的(未必是普世的)价值观——如性别和性欲平等,转化为代表文明社会和先进文化的符号,自由主义则日益成为身份政治的迷彩。
找不到导致穆斯林群体疏离的正确原因,社会治安将更难得到保证。用作者的话讲,文化主义和改革主义都忽视了“多元文化的基本问题:一种能让全社会所有人全面参与的局面,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反过来讲,那些聚集在贫民区的穆斯林变得愈发激进而非理性,并不是成心选择这样做,而是“因为工业的崩溃、歧视性的社会政策和对种族暴力的担忧”。
曾几何时,阿拉伯裔居民被视为移民中的典范——爱国、重视私有财产、比其他某些族群更少惹麻烦,然而,反恐的旗帜升起后,他们发现自己突然被逼到了角落里。在美国喜剧演员迪恩·奥贝达拉看来,“(2001年)9月10日晚上,我是个普通的白人;9月11日一觉睡醒,却变成了阿拉伯人。”通过援引统计数据,康德纳尼指出,媒体和娱乐业的渲染令反穆斯林的癔病不断传染;仅在2010年,美国针对穆斯林的暴力活动就增加了50%。
全书最后一部分讨论了犹太复国主义在欧洲的走红——根源依然是对伊斯兰的、变态的恐惧。右翼分子将穆斯林的力量归因于他们对西方政府的渗透,热衷于传播阴谋论,称腐败的统治阶级已经屈膝投降。这种情绪发展到极致,便催生了安德斯·布雷维克这种人物。
康德纳尼是英国最出色的政治作家之一,《穆斯林来了!》并非危言耸听,也不是枯燥的学术读物,而是引人入胜的描述和敏锐理解力的结合。总之,该书值得更多人去阅读,尤其是认定自己的道德优势牢不可破的自由主义者。更值得人们反思的是,作者提到,“新保守主义发明了反恐战争,奥巴马用自由主义将其常态化,就这一点,主流舆论毫无质疑。”
□英国《独立报》

本书作者主张,恐怖主义的根源在社会政策而非思想文化领域。欧美诸国对穆斯林群体特定意识形态的过度警惕和防范,只会加深隔阂,而对减少暴力无益。
比起陈词滥调的“反恐战争”之类说法,亚兰·康德纳尼聚焦恐怖主义和西方国家的反恐行动时,在遣词造句上显得更具智慧。他在新著《穆斯林来了!》的开篇写道,“恐怖主义并非极端政治的产物,而是‘政治不举’的症状。”所以,解药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强大、积极和自信的穆斯林团体,外加充分的公民权利。”但在现实中的大西洋两岸,穆斯林的意见往往被犯罪化,言论也遭到压制。如此粗鲁的方式极有可能导致暴力增多,而非减少。
在康德纳尼笔下,英美等国针对穆斯林的两种主要的防御措施——“文化主义”和“改革主义”,注重的是目标人群的意识形态,而非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说起文化主义,其头号吹鼓手当属伯纳德·路易斯,这位深受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宠信的历史学家,将问题归结于伊斯兰教本身,称“伊斯兰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同崇尚民主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基于相似的思维,另一位共和党人米特·罗姆尼如此解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分岐:“文化造成了所有不同”——换言之,数十年的占领、隔离和战争根本无所谓。
而在欧洲,作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相信,2005年巴黎郊区居民骚乱,只是因为他们是穆斯林,而与失业率高、住房条件差和警察滥权无关。或许是最荒唐的论调出自马汀·埃米斯的小品文《第二架飞机》,在文中,埃米斯轻松地承认自己一点也不懂地缘政治,但宣称自己很懂“男人”——“9·11”事件不是因为政治,而是因为涉事的穆斯林深受“性挫折”。类似的论述古已有之。笔者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的肯尼亚,就有所谓心理学家宣称,当地人的反殖民起义“并非政治因素引起,应当从精神病学方面找原因”。
至于改革主义,它的问题在于对伊斯兰文化的随意解读。作为表征,2009年,奥巴马在开罗演讲时提到,“有节制”的穆斯林文化有助于解决政治冲突。自称熟读古兰经的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则认为,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是“对伊斯兰教条的狂热迷恋”。
对穆斯林群体思想动态的关注,往往意味着国家深度介入后者的生活,以“改善信仰”。虽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有待进一步分析,穆斯林还是被笼统地分为“极端主义者”和“有节制者”。对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强调,还催生了一类所谓“美化恐怖主义罪”。随着思想文化领域成为战场,西方国家把相对新的(未必是普世的)价值观——如性别和性欲平等,转化为代表文明社会和先进文化的符号,自由主义则日益成为身份政治的迷彩。
找不到导致穆斯林群体疏离的正确原因,社会治安将更难得到保证。用作者的话讲,文化主义和改革主义都忽视了“多元文化的基本问题:一种能让全社会所有人全面参与的局面,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反过来讲,那些聚集在贫民区的穆斯林变得愈发激进而非理性,并不是成心选择这样做,而是“因为工业的崩溃、歧视性的社会政策和对种族暴力的担忧”。
曾几何时,阿拉伯裔居民被视为移民中的典范——爱国、重视私有财产、比其他某些族群更少惹麻烦,然而,反恐的旗帜升起后,他们发现自己突然被逼到了角落里。在美国喜剧演员迪恩·奥贝达拉看来,“(2001年)9月10日晚上,我是个普通的白人;9月11日一觉睡醒,却变成了阿拉伯人。”通过援引统计数据,康德纳尼指出,媒体和娱乐业的渲染令反穆斯林的癔病不断传染;仅在2010年,美国针对穆斯林的暴力活动就增加了50%。
全书最后一部分讨论了犹太复国主义在欧洲的走红——根源依然是对伊斯兰的、变态的恐惧。右翼分子将穆斯林的力量归因于他们对西方政府的渗透,热衷于传播阴谋论,称腐败的统治阶级已经屈膝投降。这种情绪发展到极致,便催生了安德斯·布雷维克这种人物。
康德纳尼是英国最出色的政治作家之一,《穆斯林来了!》并非危言耸听,也不是枯燥的学术读物,而是引人入胜的描述和敏锐理解力的结合。总之,该书值得更多人去阅读,尤其是认定自己的道德优势牢不可破的自由主义者。更值得人们反思的是,作者提到,“新保守主义发明了反恐战争,奥巴马用自由主义将其常态化,就这一点,主流舆论毫无质疑。”
□英国《独立报》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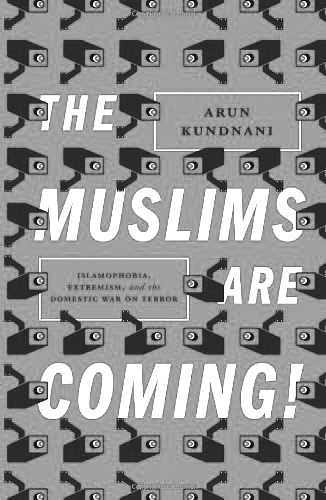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