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狂热压倒人道主义
美国“优生运动”曾拿儿童当“小白鼠”
○本报记者 高珮莙
《
青年参考
》(
2013年08月07日
22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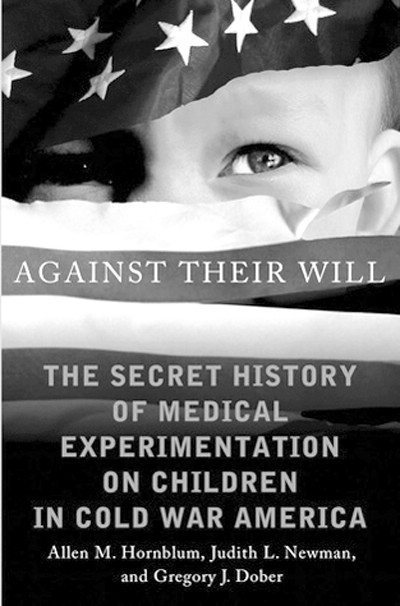 |
新书《非其所愿》封面 |
 |
弗纳德学校曾是数千名儿童的栖身之所(摄于1962年) |
二战后的几十年间,随着“优生运动”的风潮席卷美国,大批被草率定性为“白痴、低能儿”的孩子,被关进政府资助的医院、学校、孤儿院等“集中营”。他们与世隔绝,备受虐待,许多人甚至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医学研究的“小白鼠”。
时隔60年,查理·戴尔仍清楚地记得,自己加入“弗纳德科学俱乐部”的那天。他没有想到,自己充满痛苦回忆的少年岁月,会随着新书《非其所愿》在今年7月的面世而广为人知。这位72岁的退休卡车司机,因此成为英美多家媒体报道的主角。
日历翻回1954年,彼时的戴尔在马萨诸塞州的各个孤儿院辗转,总被贴上“白痴”的标签。直至来到位于沃尔瑟姆的弗纳德公立学校,情况才变得不同——这里收容的全是类似的“低能儿”。
“他们选出年纪最大的一些男孩,问我们是否愿意参加一个俱乐部。”戴尔回忆道,“我们聚在一起合计,为什么不呢?”校方许诺,参加者将得到“特殊优待”:礼物、去海边旅游、观看球赛,还会获得额外的麦片粥或牛奶作为甜点。
“简直像是过圣诞……职业棒球比赛,派对,还有一块我保存至今的米老鼠手表。”
当时并没有人告诉他,学校提供给孩子们的麦片粥和牛奶被污染过,带有很强的放射性。直到1994年,美国参议院才承认,麻省理工学院曾在弗纳德学校进行试验,让一批被蒙在鼓里的儿童定期服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食品,以进行科学研究。
“我们意识到有些事不对劲,但对真相一无所知。”多年后,戴尔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他们利用了本应该得到帮助的孩子们。”
集中营般的学校里,孩子们被用于研究
据美联社报道,弗纳德公立学校曾经秘密圈禁着上千名被认为具有生理、智力障碍的美国儿童,高峰时期多达2500多人,所有孩子无一例外,都被称为“白痴”。
同为72岁的弗雷德·鲍尔斯是戴尔的校友。1949年,鲍尔斯的养母去世,他遂被送到弗纳德学校,跟另外35个孩子挤在一间小屋里,度过了整整11年。那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光。
与其说是学校,这里更像是一座监狱。孩子们自己种蔬菜,自己缝鞋穿,还经常受到管理人员捉弄、殴打甚至性侵。长大后的鲍尔斯试着翻墙逃跑,但很快被抓了回来,又被剥光衣服关进所谓“感化中心”——一间窗户上装有铁条的禁闭室。
乔·艾梅达被经常虐待自己的父亲送进“集中营”时只有8岁。在高墙后,他从事过一项不同寻常的工作:如果有孩子死去,则取出他们的脑组织,将其切成薄片以供研究。许多样本保存至今。到了“红樱桃日”,他会跟同学围坐成一圈,管理员按字母顺序进行点名,“被点到名字的人得当众脱下裤子,被树枝狠狠抽打,直到它变得像樱桃一样红”。
跟许多类似的机构一样,弗纳德学校是一场狂热的“优生运动”的产物。从20世纪初开始流行的“优生学”观点认为,应该将基因低人一等的残疾人或有色人种与大众隔离开来,防止他们生儿育女,从而确保人类的“完美进化”。
美国作家迈克尔·安东尼奥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美国,优生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官方政策。人们被告知,通过优生运动,我们可以摆脱所有疾病,降低犯罪率,增加国民财富——只要确保将某些公民集中起来,不让他们繁衍后代。”
然而在现实中,被关进“集中营”的,多数只是贫穷、无知或被父母抛弃的孩子。拿鲍尔斯来说,他的智力水平与正常人无异,但在弗纳德学校,他还是被定性为“白痴”。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被管理者告知,自己终生属于这里(弗纳德学校),我们被告知自己不是人类种族的一部分。但我不是白痴。”鲍尔斯回忆道,“后来我想,政府之所以将我送到那儿,是因为这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他们不需要为我找一个新家,而是像丢垃圾一样将我丢弃在那个挤满人的大仓库,让我们在那里腐烂。”
纽伦堡的“文明神话”一再被打破
二战后,欧美各国的学校和媒体纷纷传播一个“快乐的神话”:1947年,对纳粹罪行的审判催生了《纽伦堡法典》,安乐死和不人道的医学实验已被这项伦理协议终结。
《纽伦堡法典》禁止医学实验和在治疗中使用“武力、欺诈、欺骗、胁迫或任何不可告人的约束或强制”,规定必须在实验前征得受试者的同意,在实验中也要避免不必要的伤害。问题在于,这份宝贵的协议,被某些利欲熏心者视若无物,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幕仍在悄然上演。
在冷战的阴影下,对世界大战的恐惧、来自苏联的核能和生物威胁,以及制药行业的蓬勃发展,令类似弗纳德学校的情形普遍存在。主要原因在于,饲养黑猩猩、豚鼠等实验动物花费昂贵,而囚犯和“白痴”本来就需要管吃管住,得到负责人批准即可随意“开发”。
在那个时代,这些非人道的试验并非出于孤立的判断失误或个别人的堕落,而是“科学主流文化的一部分”。破坏《纽伦堡法典》者,并不是虐待狂、疯子或纳粹。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囚犯、精神病人、黑人和孤儿并没有什么人权,作为“廉价而可用的实验对象”,利用他们寻找治疗致命疾病的方法没什么不合理。许多实验结果在医学或心理学期刊上公开发表,在公共学术会议上讨论,唯独没有谁为这一弱势群体说话。
英国《旁观者》杂志披露,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乔纳斯·索尔科,曾通过将小儿麻痹病毒注射给“白痴”,发明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成为公众眼中的救世主。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则评论称,雄心勃勃的医生和科学家追求自己的信仰,常常对可怕的潜在后果视而不见;在优生学的目标和应对冷战的大旗下,他们的做法不足为奇。
就这样,纽伦堡审判塑造的“文明神话”和“人道神话”一再被打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联邦政府发布报告,要求严格限制利用儿童进行医学研究,类似的举动才逐渐绝迹。
帮那些被忽视者发出声音
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万多个日日夜夜里,在弗纳德学校和全美更多同类机构,不幸沦为“小白鼠”的孩子,可能超过四位数——
1945年,在费城,麻疹患儿血液中的提取物被注入健康儿童体内,其中几十名“次品”遭到阉割。
50年代到70年代早期,史丹顿岛柳溪州立学校的几百名智障儿童在耶鲁大学的实验中,被迫摄入含病毒性肝炎患者粪便提取物的巧克力饮料,试验周期长达15年。
60年代,在纽约市皇后区的州立医院,90多名患有精神分裂症和自闭症的孩子每天被迫服用大剂量的LSD(精神致幻剂),持续了至少一年时间。
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和波士顿大学医学院,来自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将放射性碘注入儿童体内,这一项目由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门提供支持。
全美各地的几十所孤儿院和疗养院中,严重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饮食被用在孩子们身上,用以观察其健康状况的变化;研究人员让儿童接触肝炎、脑膜炎、流感、麻疹、腮腺炎、小儿麻痹等病毒,试图找到治疗方法;用淋病病毒感染智力发育迟缓的4岁男孩;让他们接受脊椎穿刺、额叶切除和电击,进而暴露于辐射或危险化学品中,更是屡见不鲜……
“他们都是被抛弃的、没人要的和受到伤害的人。”就引起轰动的《非其所愿》,作者之一艾伦·霍恩布勒姆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该书的目的正是讲述冷战时期针对儿童的秘密医学实验,“人们会感到震惊,他们不是犯人,只是些孩子。”
为了让“美国上世纪最黑暗的秘密”被公之于众,艾伦花了5年时间,与另外两名作者一起,从图书馆、档案馆、医学期刊中搜集数据,在医院和孤儿院中查阅记录,还采访了十几位曾参与测试的受害者、测试对象的亲属、医学研究成员和历史学家。
《波士顿环球报》评论称,将这些一手材料抽丝剥茧地分析,他们的作品“引人入胜而令人不安”,“既不哗众取宠也不过于空洞乏味”,更重要的是,该书揭露了一个多年存在却始终被忽视的问题:重视集体利益超过个人利益,而代价被强行施加于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
“所有信息都在那里,只是需要有人把它们汇集到一起,讲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另一位作者朱迪思·纽曼是心理学家,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医学伦理课程。他指出,“为这本书进行的努力非常艰难,希望它能帮助那些曾被忽视的孩子们,让他们发出声音。”
曾留下苦痛记忆的地方,如今成了惟一去处
时至今日,那些曾经管理过弗纳德学校的相关责任人大多已经去世。不过,很多受害者仍然健在,得益于舆论的关注,他们终于有机会令不堪回首的往昔大白于天下。
曾服用过放射性食品的查理·戴尔,如今靠收破烂和打零工维持生计。1998年,他和大约30名“弗纳德科学俱乐部”成员提起集体诉讼,通过庭外和解获得了3万美元左右的赔偿金。继续让他困扰的是,童年时期的“低能”诊断,仍赫然出现在自己的医疗记录上。
“我们告到法院,试图把它纠正过来,我们只是没受过任何教育。”他说,“他们没教我们识字,出来以后,我自己学会了很多东西。”
1960年,已经19岁的弗雷德·鲍尔斯被释放出来,但由于在“集中营”期间没有学到任何知识或技能,重获自由的他早已与社会脱节,成了旁人眼中的“盲流”。
乔·艾梅达在同一年获释。出乎所有人意料,40岁那年,他再次回到被改造为精神病院的弗纳德学校,做了一名司机,一干就是20年。
他意识到自己无家可归,曾留下苦痛记忆的人间地狱,仿佛成了惟一的去处。他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个地方夺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夺走了我最宝贵的童年。”
受害者伤痕犹在,除了公众的唏嘘,一切似乎都已风平浪静。然而,《非其所愿》一书中提到的另一个事实依然令人不安:制药公司的许多医学实验,如今被改在了第三世界国家进行。

二战后的几十年间,随着“优生运动”的风潮席卷美国,大批被草率定性为“白痴、低能儿”的孩子,被关进政府资助的医院、学校、孤儿院等“集中营”。他们与世隔绝,备受虐待,许多人甚至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医学研究的“小白鼠”。
时隔60年,查理·戴尔仍清楚地记得,自己加入“弗纳德科学俱乐部”的那天。他没有想到,自己充满痛苦回忆的少年岁月,会随着新书《非其所愿》在今年7月的面世而广为人知。这位72岁的退休卡车司机,因此成为英美多家媒体报道的主角。
日历翻回1954年,彼时的戴尔在马萨诸塞州的各个孤儿院辗转,总被贴上“白痴”的标签。直至来到位于沃尔瑟姆的弗纳德公立学校,情况才变得不同——这里收容的全是类似的“低能儿”。
“他们选出年纪最大的一些男孩,问我们是否愿意参加一个俱乐部。”戴尔回忆道,“我们聚在一起合计,为什么不呢?”校方许诺,参加者将得到“特殊优待”:礼物、去海边旅游、观看球赛,还会获得额外的麦片粥或牛奶作为甜点。
“简直像是过圣诞……职业棒球比赛,派对,还有一块我保存至今的米老鼠手表。”
当时并没有人告诉他,学校提供给孩子们的麦片粥和牛奶被污染过,带有很强的放射性。直到1994年,美国参议院才承认,麻省理工学院曾在弗纳德学校进行试验,让一批被蒙在鼓里的儿童定期服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食品,以进行科学研究。
“我们意识到有些事不对劲,但对真相一无所知。”多年后,戴尔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他们利用了本应该得到帮助的孩子们。”
集中营般的学校里,孩子们被用于研究
据美联社报道,弗纳德公立学校曾经秘密圈禁着上千名被认为具有生理、智力障碍的美国儿童,高峰时期多达2500多人,所有孩子无一例外,都被称为“白痴”。
同为72岁的弗雷德·鲍尔斯是戴尔的校友。1949年,鲍尔斯的养母去世,他遂被送到弗纳德学校,跟另外35个孩子挤在一间小屋里,度过了整整11年。那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光。
与其说是学校,这里更像是一座监狱。孩子们自己种蔬菜,自己缝鞋穿,还经常受到管理人员捉弄、殴打甚至性侵。长大后的鲍尔斯试着翻墙逃跑,但很快被抓了回来,又被剥光衣服关进所谓“感化中心”——一间窗户上装有铁条的禁闭室。
乔·艾梅达被经常虐待自己的父亲送进“集中营”时只有8岁。在高墙后,他从事过一项不同寻常的工作:如果有孩子死去,则取出他们的脑组织,将其切成薄片以供研究。许多样本保存至今。到了“红樱桃日”,他会跟同学围坐成一圈,管理员按字母顺序进行点名,“被点到名字的人得当众脱下裤子,被树枝狠狠抽打,直到它变得像樱桃一样红”。
跟许多类似的机构一样,弗纳德学校是一场狂热的“优生运动”的产物。从20世纪初开始流行的“优生学”观点认为,应该将基因低人一等的残疾人或有色人种与大众隔离开来,防止他们生儿育女,从而确保人类的“完美进化”。
美国作家迈克尔·安东尼奥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美国,优生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官方政策。人们被告知,通过优生运动,我们可以摆脱所有疾病,降低犯罪率,增加国民财富——只要确保将某些公民集中起来,不让他们繁衍后代。”
然而在现实中,被关进“集中营”的,多数只是贫穷、无知或被父母抛弃的孩子。拿鲍尔斯来说,他的智力水平与正常人无异,但在弗纳德学校,他还是被定性为“白痴”。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被管理者告知,自己终生属于这里(弗纳德学校),我们被告知自己不是人类种族的一部分。但我不是白痴。”鲍尔斯回忆道,“后来我想,政府之所以将我送到那儿,是因为这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他们不需要为我找一个新家,而是像丢垃圾一样将我丢弃在那个挤满人的大仓库,让我们在那里腐烂。”
纽伦堡的“文明神话”一再被打破
二战后,欧美各国的学校和媒体纷纷传播一个“快乐的神话”:1947年,对纳粹罪行的审判催生了《纽伦堡法典》,安乐死和不人道的医学实验已被这项伦理协议终结。
《纽伦堡法典》禁止医学实验和在治疗中使用“武力、欺诈、欺骗、胁迫或任何不可告人的约束或强制”,规定必须在实验前征得受试者的同意,在实验中也要避免不必要的伤害。问题在于,这份宝贵的协议,被某些利欲熏心者视若无物,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幕仍在悄然上演。
在冷战的阴影下,对世界大战的恐惧、来自苏联的核能和生物威胁,以及制药行业的蓬勃发展,令类似弗纳德学校的情形普遍存在。主要原因在于,饲养黑猩猩、豚鼠等实验动物花费昂贵,而囚犯和“白痴”本来就需要管吃管住,得到负责人批准即可随意“开发”。
在那个时代,这些非人道的试验并非出于孤立的判断失误或个别人的堕落,而是“科学主流文化的一部分”。破坏《纽伦堡法典》者,并不是虐待狂、疯子或纳粹。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囚犯、精神病人、黑人和孤儿并没有什么人权,作为“廉价而可用的实验对象”,利用他们寻找治疗致命疾病的方法没什么不合理。许多实验结果在医学或心理学期刊上公开发表,在公共学术会议上讨论,唯独没有谁为这一弱势群体说话。
英国《旁观者》杂志披露,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乔纳斯·索尔科,曾通过将小儿麻痹病毒注射给“白痴”,发明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成为公众眼中的救世主。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则评论称,雄心勃勃的医生和科学家追求自己的信仰,常常对可怕的潜在后果视而不见;在优生学的目标和应对冷战的大旗下,他们的做法不足为奇。
就这样,纽伦堡审判塑造的“文明神话”和“人道神话”一再被打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联邦政府发布报告,要求严格限制利用儿童进行医学研究,类似的举动才逐渐绝迹。
帮那些被忽视者发出声音
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万多个日日夜夜里,在弗纳德学校和全美更多同类机构,不幸沦为“小白鼠”的孩子,可能超过四位数——
1945年,在费城,麻疹患儿血液中的提取物被注入健康儿童体内,其中几十名“次品”遭到阉割。
50年代到70年代早期,史丹顿岛柳溪州立学校的几百名智障儿童在耶鲁大学的实验中,被迫摄入含病毒性肝炎患者粪便提取物的巧克力饮料,试验周期长达15年。
60年代,在纽约市皇后区的州立医院,90多名患有精神分裂症和自闭症的孩子每天被迫服用大剂量的LSD(精神致幻剂),持续了至少一年时间。
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和波士顿大学医学院,来自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将放射性碘注入儿童体内,这一项目由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门提供支持。
全美各地的几十所孤儿院和疗养院中,严重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饮食被用在孩子们身上,用以观察其健康状况的变化;研究人员让儿童接触肝炎、脑膜炎、流感、麻疹、腮腺炎、小儿麻痹等病毒,试图找到治疗方法;用淋病病毒感染智力发育迟缓的4岁男孩;让他们接受脊椎穿刺、额叶切除和电击,进而暴露于辐射或危险化学品中,更是屡见不鲜……
“他们都是被抛弃的、没人要的和受到伤害的人。”就引起轰动的《非其所愿》,作者之一艾伦·霍恩布勒姆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该书的目的正是讲述冷战时期针对儿童的秘密医学实验,“人们会感到震惊,他们不是犯人,只是些孩子。”
为了让“美国上世纪最黑暗的秘密”被公之于众,艾伦花了5年时间,与另外两名作者一起,从图书馆、档案馆、医学期刊中搜集数据,在医院和孤儿院中查阅记录,还采访了十几位曾参与测试的受害者、测试对象的亲属、医学研究成员和历史学家。
《波士顿环球报》评论称,将这些一手材料抽丝剥茧地分析,他们的作品“引人入胜而令人不安”,“既不哗众取宠也不过于空洞乏味”,更重要的是,该书揭露了一个多年存在却始终被忽视的问题:重视集体利益超过个人利益,而代价被强行施加于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
“所有信息都在那里,只是需要有人把它们汇集到一起,讲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另一位作者朱迪思·纽曼是心理学家,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医学伦理课程。他指出,“为这本书进行的努力非常艰难,希望它能帮助那些曾被忽视的孩子们,让他们发出声音。”
曾留下苦痛记忆的地方,如今成了惟一去处
时至今日,那些曾经管理过弗纳德学校的相关责任人大多已经去世。不过,很多受害者仍然健在,得益于舆论的关注,他们终于有机会令不堪回首的往昔大白于天下。
曾服用过放射性食品的查理·戴尔,如今靠收破烂和打零工维持生计。1998年,他和大约30名“弗纳德科学俱乐部”成员提起集体诉讼,通过庭外和解获得了3万美元左右的赔偿金。继续让他困扰的是,童年时期的“低能”诊断,仍赫然出现在自己的医疗记录上。
“我们告到法院,试图把它纠正过来,我们只是没受过任何教育。”他说,“他们没教我们识字,出来以后,我自己学会了很多东西。”
1960年,已经19岁的弗雷德·鲍尔斯被释放出来,但由于在“集中营”期间没有学到任何知识或技能,重获自由的他早已与社会脱节,成了旁人眼中的“盲流”。
乔·艾梅达在同一年获释。出乎所有人意料,40岁那年,他再次回到被改造为精神病院的弗纳德学校,做了一名司机,一干就是20年。
他意识到自己无家可归,曾留下苦痛记忆的人间地狱,仿佛成了惟一的去处。他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个地方夺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夺走了我最宝贵的童年。”
受害者伤痕犹在,除了公众的唏嘘,一切似乎都已风平浪静。然而,《非其所愿》一书中提到的另一个事实依然令人不安:制药公司的许多医学实验,如今被改在了第三世界国家进行。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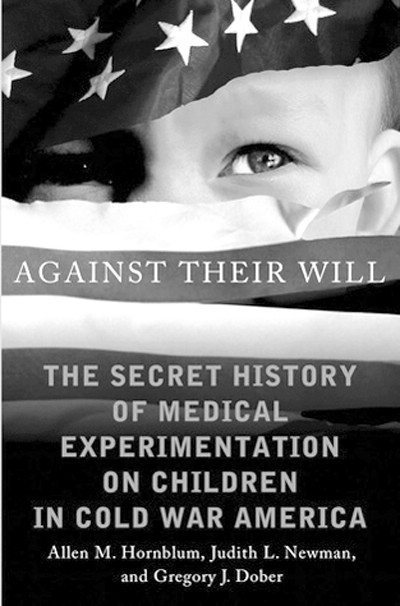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