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逃兵:不寻常的二战生存故事
作者 [英] 尼尔·阿彻森 译者 韦盖利
《
青年参考
》(
2013年04月10日
32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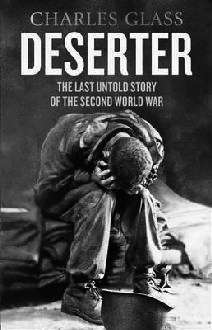 |
《逃亡者:鲜为人知的二战故事》(Deserter: The Untold Story of WWII),哈珀出版社2013年3月,400页。 |
比起战争英雄,逃兵的故事同样扣人心弦,而且距真实更近一步。
当逃兵固然称不上光彩,但此类现象在战争期间并不鲜见。促使士兵放弃职责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可能由于家庭问题,可能因为与军官不合,或者是出于对杀人的恐惧。当然,最明显、最普遍的动机是:希望藉此逃避那些可能打爆他们的头,或者用刺刀刺穿他们身体的敌人。普罗大众不甚了解的,并非士兵们为何逃跑,而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为何不逃跑——即使在面临不可避免的失败时,他们依然坚守阵地,直到射出最后一发子弹。
这就是查尔斯·格拉斯在新书《逃亡者》中探讨的问题。格拉斯复原了三位年轻男人——说男孩可能更合适——投身于残酷的欧洲战场,参战,逃跑,回到部队,再度开小差的复杂经历。史蒂夫·韦斯来自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阿尔弗雷德·怀特黑德出身于田纳西州的贫困乡村;约翰·白恩是英国人,急切地盼望逃离虐待狂父亲。
三人都不是高大全的英雄。他们目睹了令人心碎的可怕事物,或者受到女人、酒精和财富的诱惑,或者被炮击和轰炸吓坏,或者突然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过几天就会死去。
据作者统计,二战中有“差不多5万美军逃兵和10万英军逃兵”,其中80%是从前线逃走的,几乎都在欧洲战区“当过炮灰”。旷日持久的冲突落幕时,伦敦、巴黎以及那不勒斯等一些主要城市中,不时可见荷枪实弹的、擅离职守的军人,他们的很多人被抢劫团伙和军需品贩子招募。正规军不得不加派兵力保护输送给养的火车,因为这些火车在混乱的欧洲常常被抢劫。在巴黎,夜间时常爆发警察和“美国土匪”的枪战,俨然成了新的洛杉矶。
不过,格拉斯笔下的三名主人公并未从一开始就退缩。韦斯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时才18岁。在化作废墟的城市,他第一次见到被抓获的逃兵谩骂上司,发现朋友因为“战斗疲劳”而崩溃或尸横就地。在战场上,他随时可能被炮弹炸死、被狙击手击毙。无数次,他筋疲力尽、孤独地被雨淋得透湿,在疲惫和恐怖中泪流满面地呼唤着母亲。
使三位主角坚持下来的是战友的情谊:朋友间的信任,经验丰富的老兵的援手。对在诺曼底登陆中幸存的怀特黑德来说,他的田纳西州老乡“彩弹”提供的支持最大。而在白恩的记忆中,满嘴脏话却忠诚老实的战友休吉使他挺了过来。“战争是疯狂的,军队是无情的,但战友从来不会让你沮丧,有了他们,你就能承担难以忍受的痛苦。”
然而,在法国孚日山脉附近,韦斯发现自己的密友都已殉职,与之类似,“彩弹”踩到地雷死去,休吉被迫击炮打死。心灵力量的耗竭,使三个年轻人再也无法支撑下去。
怀特黑德在混乱的巴黎沦为一名匪徒。韦斯带着几名同伴踏雪逃离,一度被关进军事监狱,最后回到加州,成为一名精神病专家。白恩在突尼斯就当过一回逃兵,战争结束后,他等不及复员,又一次不辞而别,遁入伦敦的深巷中,后来成了诗人和业余拳击手。
应该说,《逃亡者》无意对逃兵这种现象进行学术探讨,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三个男人讲述的“自己的战争”,这些故事是在常人无法想象的恐惧和痛苦重压下、濒临崩溃的个体的真实经历,无疑是曲折跌宕、令人难忘的,是从历史的泥沼中打捞出来的珍贵碎片。和笔者一样,相信多数人都会牢牢记住这些场景:白恩从死去的战友身上搜寻遗物,韦斯为因强奸而被处决的黑人士兵祈祷,怀特黑德在巴黎的公路上打劫了一辆运送物资的军车……
格拉斯在每章开头引用了1943年出版的《士兵心理学》一书的精彩论述,同样让人印象深刻。“放弃是保护有机体不受太多苦痛的自然方式”;以及,“在任何一支军队里,都有一些不懂得害怕的男人——但这部分人是不正常的”。上述道理显而易见吗?或许吧。可是,战争的疯狂,使“说出显而易见的道理”都成了需要经过斗争才能取得的权利。
英国《卫报》

比起战争英雄,逃兵的故事同样扣人心弦,而且距真实更近一步。
当逃兵固然称不上光彩,但此类现象在战争期间并不鲜见。促使士兵放弃职责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可能由于家庭问题,可能因为与军官不合,或者是出于对杀人的恐惧。当然,最明显、最普遍的动机是:希望藉此逃避那些可能打爆他们的头,或者用刺刀刺穿他们身体的敌人。普罗大众不甚了解的,并非士兵们为何逃跑,而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为何不逃跑——即使在面临不可避免的失败时,他们依然坚守阵地,直到射出最后一发子弹。
这就是查尔斯·格拉斯在新书《逃亡者》中探讨的问题。格拉斯复原了三位年轻男人——说男孩可能更合适——投身于残酷的欧洲战场,参战,逃跑,回到部队,再度开小差的复杂经历。史蒂夫·韦斯来自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阿尔弗雷德·怀特黑德出身于田纳西州的贫困乡村;约翰·白恩是英国人,急切地盼望逃离虐待狂父亲。
三人都不是高大全的英雄。他们目睹了令人心碎的可怕事物,或者受到女人、酒精和财富的诱惑,或者被炮击和轰炸吓坏,或者突然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过几天就会死去。
据作者统计,二战中有“差不多5万美军逃兵和10万英军逃兵”,其中80%是从前线逃走的,几乎都在欧洲战区“当过炮灰”。旷日持久的冲突落幕时,伦敦、巴黎以及那不勒斯等一些主要城市中,不时可见荷枪实弹的、擅离职守的军人,他们的很多人被抢劫团伙和军需品贩子招募。正规军不得不加派兵力保护输送给养的火车,因为这些火车在混乱的欧洲常常被抢劫。在巴黎,夜间时常爆发警察和“美国土匪”的枪战,俨然成了新的洛杉矶。
不过,格拉斯笔下的三名主人公并未从一开始就退缩。韦斯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时才18岁。在化作废墟的城市,他第一次见到被抓获的逃兵谩骂上司,发现朋友因为“战斗疲劳”而崩溃或尸横就地。在战场上,他随时可能被炮弹炸死、被狙击手击毙。无数次,他筋疲力尽、孤独地被雨淋得透湿,在疲惫和恐怖中泪流满面地呼唤着母亲。
使三位主角坚持下来的是战友的情谊:朋友间的信任,经验丰富的老兵的援手。对在诺曼底登陆中幸存的怀特黑德来说,他的田纳西州老乡“彩弹”提供的支持最大。而在白恩的记忆中,满嘴脏话却忠诚老实的战友休吉使他挺了过来。“战争是疯狂的,军队是无情的,但战友从来不会让你沮丧,有了他们,你就能承担难以忍受的痛苦。”
然而,在法国孚日山脉附近,韦斯发现自己的密友都已殉职,与之类似,“彩弹”踩到地雷死去,休吉被迫击炮打死。心灵力量的耗竭,使三个年轻人再也无法支撑下去。
怀特黑德在混乱的巴黎沦为一名匪徒。韦斯带着几名同伴踏雪逃离,一度被关进军事监狱,最后回到加州,成为一名精神病专家。白恩在突尼斯就当过一回逃兵,战争结束后,他等不及复员,又一次不辞而别,遁入伦敦的深巷中,后来成了诗人和业余拳击手。
应该说,《逃亡者》无意对逃兵这种现象进行学术探讨,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三个男人讲述的“自己的战争”,这些故事是在常人无法想象的恐惧和痛苦重压下、濒临崩溃的个体的真实经历,无疑是曲折跌宕、令人难忘的,是从历史的泥沼中打捞出来的珍贵碎片。和笔者一样,相信多数人都会牢牢记住这些场景:白恩从死去的战友身上搜寻遗物,韦斯为因强奸而被处决的黑人士兵祈祷,怀特黑德在巴黎的公路上打劫了一辆运送物资的军车……
格拉斯在每章开头引用了1943年出版的《士兵心理学》一书的精彩论述,同样让人印象深刻。“放弃是保护有机体不受太多苦痛的自然方式”;以及,“在任何一支军队里,都有一些不懂得害怕的男人——但这部分人是不正常的”。上述道理显而易见吗?或许吧。可是,战争的疯狂,使“说出显而易见的道理”都成了需要经过斗争才能取得的权利。
英国《卫报》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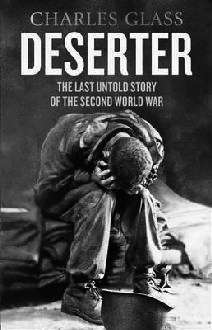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