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的古拉格是这样诞生的
作者 [美] 安妮·阿普尔鲍姆 译者 戴大洪
《
青年参考
》(
2013年03月27日
33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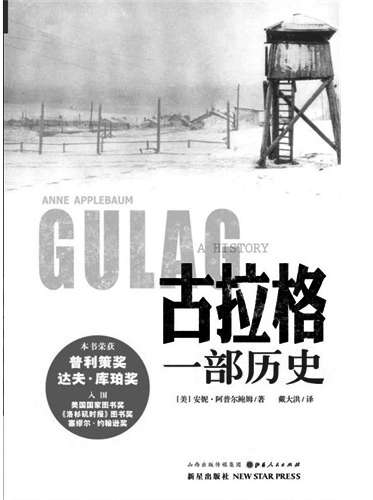 |
|
大革命期间独特的政治逻辑,令一类“专设集中营”与苏维埃俄国几乎同步建立。
1917年,革命浪潮迅速席卷俄罗斯,帝俄社会仿佛纸板搭成的房子一样土崩瓦解。在沙皇尼古拉二世于2月份退位以后,事态发展证明,革命已极难平息或控制。临时政府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后来写道,在随着旧政权的崩溃而出现的真空里,“现有的所有政治和政策方案,无论是大胆想象的还是精心构思的,全都漫无目的和用途地横空出世了”。
常规监狱满足不了需求
十月革命之后不到几个星期,列宁就亲自要求“采取严厉措施以立即改善对彼得格勒监狱的食品供应”。几个月后,莫斯科的一名契卡(全俄肃反及消除怠工特设委员会)官员在视察了本市的监狱后报告说,监狱里“寒冷肮脏得可怕”,而且流行斑疹伤寒,囚犯们都在挨饿。某张报纸刊登的一篇文章声称,设计容量为1000人的莫斯科布特尔卡监狱已经关押了2500人。另一张报纸则不满地说,赤卫队“每天毫无计划地逮捕成百上千人,然后却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
新的当权者只好把犯人关进地下室、阁楼、闲置的宫殿和旧教堂。1917年12月,契卡的一个委员会就讨论过关押在斯莫尔尼宫——列宁在彼得格勒的指挥部——地下室里的56名不同类型的囚犯的命运,这些囚犯包括“窃贼、酒鬼和各种类型的‘政治犯’”。
并不是所有人都因这种混乱状态而遭殃。R·B·洛克哈特是一名受到从事间谍活动指控的英国外交官,1918年时被关押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房间里。他把大量时间用来玩单人纸牌,而且阅读修昔底德和卡莱尔的书籍。一名以前的宫廷侍者不时给他送来热茶和报纸。
即使是在传统监狱继续发挥作用期间,管理制度也不稳定,而且监狱看守缺乏经验。有苏联官员对这一时期回忆道,“不逃跑的只是那些实在懒惰的人”。
混乱迫使契卡寻找新的解决办法:布尔什维克党几乎不可能允许将其“真正的”敌人关押在普通监狱系统。混乱的监狱和懒惰的看守也许适合看管扒手和少年犯,却不适合看管“怠工者、寄生虫、投机商、白军军官、神职人员、资本家”以及革命领袖们能想得到的、其他具有严重威胁的人,因此,需要找到更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
“红色恐怖”的关键一环
解决办法找到了。早在1918年6月,托洛茨基曾要求安抚一群难以管束的捷克战俘,消除他们的敌意,并把他们安置在一个集中营里。12天后,在一份备忘录中,托洛茨基再次谈起了集中营,在这种露天的监狱里,“城市和乡村的资产阶级……将被动员起来组成专干脏活累活的后勤队。那些拒绝者将被处以罚款,在缴纳罚款之前要把他们扣押起来”。
8月,列宁也使用了这个词。他要求“对富农、神职人员和白卫军采取大规模恐怖行动”,并把那些“不可靠分子”“关押在城外的集中营里”。设施这时已经到位——1918年夏天,随着布列斯特和约签订,苏维埃政权释放了200万名战俘,闲置的战俘营立即移交给了契卡。
就利用“专设”集中营监禁“敌人”来说,契卡应当是接管这项工作的理想机构。作为一个全新的组织,契卡被设计成党的“剑与盾”,不对苏维埃政府及其任何部门负责。同年9月,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接到指示,要求契卡贯彻执行列宁的“红色恐怖”政策。《红星报》这样作了描述:“没有怜悯,没有宽恕,我们要对敌人大开杀戒……让他们被自己的血泊所淹没。为了列宁流出的血……我们要让资产阶级血流成河——让他们流血流得越多越好……”
“专设集中营”对红色恐怖至关重要。关于红色恐怖的第一项法令,不仅要求逮捕并监禁“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地主、工厂主、商人、反革命的神职人员、反苏维埃的军官”,而且要把他们“用集中营隔离起来”。尽管没有关于囚犯人数的可靠数字,到1919年底时,全国范围内已经有了21个记录在案的集中营,又过了一年,这类设施的数量达到了107个。
在这个阶段,集中营的目的仍然不够明确。囚犯必须从事劳动——为了什么目的?劳动教育改造?还是为了羞辱他们?或者认为这是帮助建设苏维埃的新国家?不同的领导人和不同的机构有各自不同的答案。1919年2月,捷尔任斯基本人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说,鼓吹集中营的教育改造作用,称“我们将以这种方式创办劳动的学校”。
实用主义考虑占了上风
可是,当关于专设集中营的第一批法令颁布时,略有不同的考虑似乎占了上风。由于国家拨款数额的多少不定,集中营的管理者们很快就对自筹资金的主意产生了兴趣,或者至少是对实际利用他们的囚犯产生了兴趣。
1919年秋,一份给捷尔任斯基的报告建议,“把那些不能劳动的人送到别处去”,从而使集中营的效率更高——这是后来被古拉格的领导人多次采用的一种策略。集中营的管理者已经开始关心疾病和饥饿,主要原因在于生病和饥饿的囚犯是不能干活儿的。至于囚犯的尊严和人格,更不必说他们的生存,几乎很难引起他们的注意。
当然,并非所有集中营负责人都关心对囚犯进行教育改造或者自筹资金的问题。某些人倒是更喜欢通过羞辱的方式惩罚这些以前的富人,让后者体验一下劳动者的命运。一份来自乌克兰波尔塔瓦市的报告特别提到,“布尔什维克给逮捕的资产阶级分子分派劳动任务,打算以此作为一种嘲弄人的手段,尽力贬低他们的身份。例如,一名囚犯……被迫用手清理地上厚厚的一层脏东西。命令另一名囚犯打扫厕所,而且……只给他一块抹布干这个活儿”。
有一点是清楚的:到内战结束时,新政权已明显地形成了两个分立的监狱系统,具有不同的行为准则,不同的思维方式。契卡——后来的克格勃,控制着被称为“专设集中营”或“特别集中营”的特殊监狱。它们处于其他苏维埃机构的管辖范围和公众视线之外,管理更严格,对逃跑的惩罚更严厉,其中的囚犯,也没有必要先由普通法庭判决有罪。
摘自《古拉格:一部历史》,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

大革命期间独特的政治逻辑,令一类“专设集中营”与苏维埃俄国几乎同步建立。
1917年,革命浪潮迅速席卷俄罗斯,帝俄社会仿佛纸板搭成的房子一样土崩瓦解。在沙皇尼古拉二世于2月份退位以后,事态发展证明,革命已极难平息或控制。临时政府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后来写道,在随着旧政权的崩溃而出现的真空里,“现有的所有政治和政策方案,无论是大胆想象的还是精心构思的,全都漫无目的和用途地横空出世了”。
常规监狱满足不了需求
十月革命之后不到几个星期,列宁就亲自要求“采取严厉措施以立即改善对彼得格勒监狱的食品供应”。几个月后,莫斯科的一名契卡(全俄肃反及消除怠工特设委员会)官员在视察了本市的监狱后报告说,监狱里“寒冷肮脏得可怕”,而且流行斑疹伤寒,囚犯们都在挨饿。某张报纸刊登的一篇文章声称,设计容量为1000人的莫斯科布特尔卡监狱已经关押了2500人。另一张报纸则不满地说,赤卫队“每天毫无计划地逮捕成百上千人,然后却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
新的当权者只好把犯人关进地下室、阁楼、闲置的宫殿和旧教堂。1917年12月,契卡的一个委员会就讨论过关押在斯莫尔尼宫——列宁在彼得格勒的指挥部——地下室里的56名不同类型的囚犯的命运,这些囚犯包括“窃贼、酒鬼和各种类型的‘政治犯’”。
并不是所有人都因这种混乱状态而遭殃。R·B·洛克哈特是一名受到从事间谍活动指控的英国外交官,1918年时被关押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房间里。他把大量时间用来玩单人纸牌,而且阅读修昔底德和卡莱尔的书籍。一名以前的宫廷侍者不时给他送来热茶和报纸。
即使是在传统监狱继续发挥作用期间,管理制度也不稳定,而且监狱看守缺乏经验。有苏联官员对这一时期回忆道,“不逃跑的只是那些实在懒惰的人”。
混乱迫使契卡寻找新的解决办法:布尔什维克党几乎不可能允许将其“真正的”敌人关押在普通监狱系统。混乱的监狱和懒惰的看守也许适合看管扒手和少年犯,却不适合看管“怠工者、寄生虫、投机商、白军军官、神职人员、资本家”以及革命领袖们能想得到的、其他具有严重威胁的人,因此,需要找到更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
“红色恐怖”的关键一环
解决办法找到了。早在1918年6月,托洛茨基曾要求安抚一群难以管束的捷克战俘,消除他们的敌意,并把他们安置在一个集中营里。12天后,在一份备忘录中,托洛茨基再次谈起了集中营,在这种露天的监狱里,“城市和乡村的资产阶级……将被动员起来组成专干脏活累活的后勤队。那些拒绝者将被处以罚款,在缴纳罚款之前要把他们扣押起来”。
8月,列宁也使用了这个词。他要求“对富农、神职人员和白卫军采取大规模恐怖行动”,并把那些“不可靠分子”“关押在城外的集中营里”。设施这时已经到位——1918年夏天,随着布列斯特和约签订,苏维埃政权释放了200万名战俘,闲置的战俘营立即移交给了契卡。
就利用“专设”集中营监禁“敌人”来说,契卡应当是接管这项工作的理想机构。作为一个全新的组织,契卡被设计成党的“剑与盾”,不对苏维埃政府及其任何部门负责。同年9月,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接到指示,要求契卡贯彻执行列宁的“红色恐怖”政策。《红星报》这样作了描述:“没有怜悯,没有宽恕,我们要对敌人大开杀戒……让他们被自己的血泊所淹没。为了列宁流出的血……我们要让资产阶级血流成河——让他们流血流得越多越好……”
“专设集中营”对红色恐怖至关重要。关于红色恐怖的第一项法令,不仅要求逮捕并监禁“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地主、工厂主、商人、反革命的神职人员、反苏维埃的军官”,而且要把他们“用集中营隔离起来”。尽管没有关于囚犯人数的可靠数字,到1919年底时,全国范围内已经有了21个记录在案的集中营,又过了一年,这类设施的数量达到了107个。
在这个阶段,集中营的目的仍然不够明确。囚犯必须从事劳动——为了什么目的?劳动教育改造?还是为了羞辱他们?或者认为这是帮助建设苏维埃的新国家?不同的领导人和不同的机构有各自不同的答案。1919年2月,捷尔任斯基本人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说,鼓吹集中营的教育改造作用,称“我们将以这种方式创办劳动的学校”。
实用主义考虑占了上风
可是,当关于专设集中营的第一批法令颁布时,略有不同的考虑似乎占了上风。由于国家拨款数额的多少不定,集中营的管理者们很快就对自筹资金的主意产生了兴趣,或者至少是对实际利用他们的囚犯产生了兴趣。
1919年秋,一份给捷尔任斯基的报告建议,“把那些不能劳动的人送到别处去”,从而使集中营的效率更高——这是后来被古拉格的领导人多次采用的一种策略。集中营的管理者已经开始关心疾病和饥饿,主要原因在于生病和饥饿的囚犯是不能干活儿的。至于囚犯的尊严和人格,更不必说他们的生存,几乎很难引起他们的注意。
当然,并非所有集中营负责人都关心对囚犯进行教育改造或者自筹资金的问题。某些人倒是更喜欢通过羞辱的方式惩罚这些以前的富人,让后者体验一下劳动者的命运。一份来自乌克兰波尔塔瓦市的报告特别提到,“布尔什维克给逮捕的资产阶级分子分派劳动任务,打算以此作为一种嘲弄人的手段,尽力贬低他们的身份。例如,一名囚犯……被迫用手清理地上厚厚的一层脏东西。命令另一名囚犯打扫厕所,而且……只给他一块抹布干这个活儿”。
有一点是清楚的:到内战结束时,新政权已明显地形成了两个分立的监狱系统,具有不同的行为准则,不同的思维方式。契卡——后来的克格勃,控制着被称为“专设集中营”或“特别集中营”的特殊监狱。它们处于其他苏维埃机构的管辖范围和公众视线之外,管理更严格,对逃跑的惩罚更严厉,其中的囚犯,也没有必要先由普通法庭判决有罪。
摘自《古拉格:一部历史》,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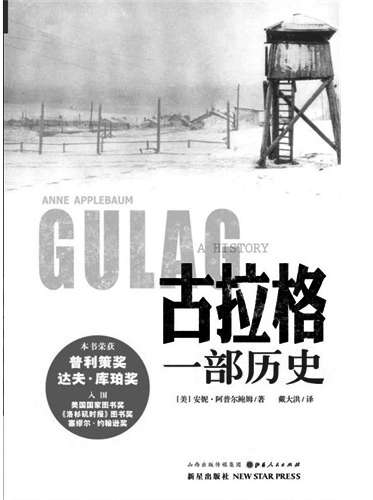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