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电影人:发掘胶片里的希特勒
○本报记者 高珮莙
《
青年参考
》(
2013年03月20日
30
版)
 |
爱娃手持16毫米摄影机拍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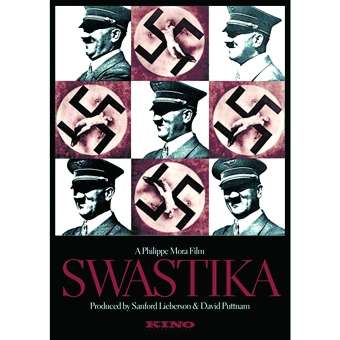 |
《邪恶纳粹》海报 |
 |
希特勒与爱娃 |
 |
爱娃 |
 |
希特勒 |
如果没有手持16毫米摄影机的爱娃·布劳恩,希特勒不为人知的一面不会被记录下来。如果没有德国电影人卢茨·贝克尔的痴迷和执著,这些震惊世界的画面也许会永远尘封于历史的某个角落。
被送进黑暗深渊的一代从未停止关于希特勒的思考
爬出防空洞的瞬间,卢茨·贝克尔眼中的世界是一片废墟。士兵横尸街头,苍蝇嗡嗡作响。废墟之下,是遮掩不住的死亡气息。
那是1945年的柏林,贝克尔4岁。
贝克尔没有见过属于第三帝国的荣耀。他的童年在柏林地下的防空洞中度过,防空洞里的恶臭和恐怖在他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盟军的飞机时常来袭,整个城市变成了燃烧的废墟。炸弹落下,即使落在遥远的地方,防空洞中的气压也会变得极大。
“人们常常从耳朵、鼻子和眼睛中流出血来,我总是耳聋、耳鸣。”他说,“我真羡慕那些不曾在恐惧中长大的孩子。”
第三帝国给贝克尔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创伤。
随着二战结束,关于世界上最邪恶政权之一的可怕真相开始泄露出来。第一批屈服于这些真相的德国人,是那些在柏林的陷落中大难不死的孩子——像贝克尔这样的年轻人。
“我出生在一个谎言的世界里,”贝克尔说,“我们是被送进黑暗深渊的一代。”
从那时起,贝克尔从未停止关于希特勒的思考,还有这位领袖给德国人带来了什么。这位卓越的艺术家和电影历史学家,将他的大部分人生献给了希特勒。
“孩提时我被禁止说脏话,现在,我会站在母亲卧室的梳妆镜前,重复‘狗屎’这样的字眼儿,”他一边说一边大笑,“这时我心里想的是希特勒。”
此时,这位第三帝国的幸存者住在英国伦敦贝斯沃特郡,年过古稀。
历史就藏在这些小小的胶片里
20世纪50年代,贝克尔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作为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的天赋,决定将其作为终身职业。
1966年,他到伦敦求学,与日后的著名导演大卫·斯雷德、德里克·加曼做同学。
在写论文的过程中,贝克尔意外地有了新发现。
“就在德国联邦档案馆,”贝克尔回忆道,“我第一次发现了爱娃·布劳恩手持16毫米西门子摄影机的照片。”
这让贝克尔想起了关于爱娃家庭录像的传言。一直没有人知道这些录像被藏在哪里,就连它们是否存在都无法证实。
贝克尔相信,如果有摄影机,那一定有录像;如果有录像,它一定被保存在某个地方。
贝克尔开始了苦苦摸索,不肯放弃任何线索。
“那时候并不流行将录像视为历史的见证。”他回忆道,“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报纸比录像更重要。但我有一个非常急迫的需要,想要整理自己的过去。”
也许只有一个在纳粹柏林长大的孩子,才能有这种迫切的需要。毕竟,在那个年代,希特勒的情人爱娃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贝克尔查找了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和国家电影资料馆的记录,然后辗转到了美国。
1970年4月,贝克尔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参加一次电影爱好者聚会,结识了一位二战老兵。
这位老兵告诉贝克尔,他的确曾在希特勒的巢穴中看到成堆的电影胶片,只是当时并未意识到它们的价值。他记得,这些材料被美国陆军通信兵带走了。
这一线索让贝克尔兴奋不已。假如它们存在,他推测,这些胶片最终会被送到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怀着期待的贝克尔依然徒劳无功,但他没有放弃。“一定有这些录像。”
关键在于16毫米摄影机。就录像档案来说,35毫米的优于16毫米的,因此,在胶片碎掉或消失之前,档案馆往往会优先考虑保存35毫米的录像。
一次华盛顿之行中,贝克尔偶然发现了一个新线索——在郊区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旧飞机机库,可能保存着一批16毫米录像。
1972年春季的一天,贝克尔开车出城,来到这个机库,开始在一堆生锈的废旧金属罐中搜寻,一套贴着德文标签的金属罐闯入眼帘。
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他打开了第一个罐子。历史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就藏在这些小小的胶片里。
摄影机以罕见的亲密方式接近希特勒
认识德国最有权势的人之前,爱娃只是个普通的17岁金发少女,漂亮,活泼,为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担任助理。
当时,霍夫曼的任务就是打造希特勒的对外形象,使他始终被视为一个坚定而目空一切的人物,一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英雄。爱娃的出现,让希特勒的形象完全不同。
在爱娃的镜头中,希特勒和几个纳粹高层人物在阳台上晒太阳,喝着咖啡聊着天,互相开玩笑,不时拿起一块蛋糕,偶尔为拍摄者摆一个姿势。
爱娃手中的摄影机以罕见的亲密方式接近希特勒。当亲信之外的访客出现时,摄影机会退到一个更加敬而远之的距离。
举办家庭聚会时,客人们穿着他们最好的礼服到访,希特勒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带着和蔼可亲的笑容招呼客人,偶尔与顾问交谈,或跟爱犬玩耍。希特勒与孩子们围坐桌前,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叔叔一样主持聚会。
胶片中的大部分画面是彩色的,有种扑面而来的真实感,希特勒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邪恶者的平凡”。没人能看得出,就是这群文质彬彬的客人,让欧洲大陆伏尸百万。
这些胶片拍摄于1941年夏,正是希特勒纳粹事业的巅峰,胜利似乎触手可及。
有了适合的土壤,任何国家都有可能走上同样黑暗的道路
1973年5月,贝克尔用爱娃家庭录像中的材料制作了纪录片《邪恶纳粹》,在戛纳电影节上首映。
《邪恶纳粹》塑造了一个与人们的印象完全不同的希特勒。除了私人生活中的温和、友善,影片中的希特勒也饱受民众由衷的爱戴和崇拜。
男女老少蜂拥而至,带着满脸的兴奋和激动,一心想瞻仰元首的仪容,警卫几乎无法阻止;鲜花撒在他经过的路旁;希特勒对孩子们微笑,逗一逗年轻的姑娘,给骄傲的小伙子们赞许的笑容;一位从数百人中脱颖而出,得以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担任鼓手的年轻人,看起来像是地球上最幸福的男孩。
影片中的德国人似乎无比团结和幸福,每个人都在巨大的国家机器中各得其所。他们似乎都在为理想奋斗,而不是为了金钱或是自私的目的,就连纳粹分子都面带笑容。直到影片的最后,战争、大屠杀等人们熟悉的画面才出现。
这部另类的影片迅速激起了人们的反感,甚至引发了暴力事件。这部纪录片在德国被禁了37年。
令人们不安的是,希特勒不是淌着口水的恶魔或肮脏的怪物,纳粹是与我们一般无二的人。胜利者们不愿意去想:有了适合的土壤,任何国家都有可能走上同样黑暗的道路。
这些情绪,都曾经出现在第一次看到爱娃录像的贝克尔身上。“我一直处于一种极度的兴奋中,仿佛我的生命有一种使命。我对纳粹感到愤怒,现在,我终于可以通过一种积极的方式来疏导、宣泄这些愤怒。”
如今,很多人可以以全新的视角看待第三帝国,愤怒转变为理智的审视,妖魔不再被视为妖魔,而是一个常人——即使是来自人性阴暗面的邪恶使者,也仍然是人。
对贝克尔来说,回顾爱娃的家庭录像仍然是痛苦的,人们对《邪恶纳粹》的反应也折磨着他,只不过,回顾往事,他已学会与过去和解。
“我的研究不是什么巨大的胜利,顶多是休战协议。我能够看到,过去被放进历史书里,纳粹不再像幽灵般出没。我的旅程已经结束。”

如果没有手持16毫米摄影机的爱娃·布劳恩,希特勒不为人知的一面不会被记录下来。如果没有德国电影人卢茨·贝克尔的痴迷和执著,这些震惊世界的画面也许会永远尘封于历史的某个角落。
被送进黑暗深渊的一代从未停止关于希特勒的思考
爬出防空洞的瞬间,卢茨·贝克尔眼中的世界是一片废墟。士兵横尸街头,苍蝇嗡嗡作响。废墟之下,是遮掩不住的死亡气息。
那是1945年的柏林,贝克尔4岁。
贝克尔没有见过属于第三帝国的荣耀。他的童年在柏林地下的防空洞中度过,防空洞里的恶臭和恐怖在他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盟军的飞机时常来袭,整个城市变成了燃烧的废墟。炸弹落下,即使落在遥远的地方,防空洞中的气压也会变得极大。
“人们常常从耳朵、鼻子和眼睛中流出血来,我总是耳聋、耳鸣。”他说,“我真羡慕那些不曾在恐惧中长大的孩子。”
第三帝国给贝克尔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创伤。
随着二战结束,关于世界上最邪恶政权之一的可怕真相开始泄露出来。第一批屈服于这些真相的德国人,是那些在柏林的陷落中大难不死的孩子——像贝克尔这样的年轻人。
“我出生在一个谎言的世界里,”贝克尔说,“我们是被送进黑暗深渊的一代。”
从那时起,贝克尔从未停止关于希特勒的思考,还有这位领袖给德国人带来了什么。这位卓越的艺术家和电影历史学家,将他的大部分人生献给了希特勒。
“孩提时我被禁止说脏话,现在,我会站在母亲卧室的梳妆镜前,重复‘狗屎’这样的字眼儿,”他一边说一边大笑,“这时我心里想的是希特勒。”
此时,这位第三帝国的幸存者住在英国伦敦贝斯沃特郡,年过古稀。
历史就藏在这些小小的胶片里
20世纪50年代,贝克尔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作为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的天赋,决定将其作为终身职业。
1966年,他到伦敦求学,与日后的著名导演大卫·斯雷德、德里克·加曼做同学。
在写论文的过程中,贝克尔意外地有了新发现。
“就在德国联邦档案馆,”贝克尔回忆道,“我第一次发现了爱娃·布劳恩手持16毫米西门子摄影机的照片。”
这让贝克尔想起了关于爱娃家庭录像的传言。一直没有人知道这些录像被藏在哪里,就连它们是否存在都无法证实。
贝克尔相信,如果有摄影机,那一定有录像;如果有录像,它一定被保存在某个地方。
贝克尔开始了苦苦摸索,不肯放弃任何线索。
“那时候并不流行将录像视为历史的见证。”他回忆道,“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报纸比录像更重要。但我有一个非常急迫的需要,想要整理自己的过去。”
也许只有一个在纳粹柏林长大的孩子,才能有这种迫切的需要。毕竟,在那个年代,希特勒的情人爱娃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贝克尔查找了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和国家电影资料馆的记录,然后辗转到了美国。
1970年4月,贝克尔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参加一次电影爱好者聚会,结识了一位二战老兵。
这位老兵告诉贝克尔,他的确曾在希特勒的巢穴中看到成堆的电影胶片,只是当时并未意识到它们的价值。他记得,这些材料被美国陆军通信兵带走了。
这一线索让贝克尔兴奋不已。假如它们存在,他推测,这些胶片最终会被送到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怀着期待的贝克尔依然徒劳无功,但他没有放弃。“一定有这些录像。”
关键在于16毫米摄影机。就录像档案来说,35毫米的优于16毫米的,因此,在胶片碎掉或消失之前,档案馆往往会优先考虑保存35毫米的录像。
一次华盛顿之行中,贝克尔偶然发现了一个新线索——在郊区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旧飞机机库,可能保存着一批16毫米录像。
1972年春季的一天,贝克尔开车出城,来到这个机库,开始在一堆生锈的废旧金属罐中搜寻,一套贴着德文标签的金属罐闯入眼帘。
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他打开了第一个罐子。历史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就藏在这些小小的胶片里。
摄影机以罕见的亲密方式接近希特勒
认识德国最有权势的人之前,爱娃只是个普通的17岁金发少女,漂亮,活泼,为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担任助理。
当时,霍夫曼的任务就是打造希特勒的对外形象,使他始终被视为一个坚定而目空一切的人物,一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英雄。爱娃的出现,让希特勒的形象完全不同。
在爱娃的镜头中,希特勒和几个纳粹高层人物在阳台上晒太阳,喝着咖啡聊着天,互相开玩笑,不时拿起一块蛋糕,偶尔为拍摄者摆一个姿势。
爱娃手中的摄影机以罕见的亲密方式接近希特勒。当亲信之外的访客出现时,摄影机会退到一个更加敬而远之的距离。
举办家庭聚会时,客人们穿着他们最好的礼服到访,希特勒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带着和蔼可亲的笑容招呼客人,偶尔与顾问交谈,或跟爱犬玩耍。希特勒与孩子们围坐桌前,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叔叔一样主持聚会。
胶片中的大部分画面是彩色的,有种扑面而来的真实感,希特勒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邪恶者的平凡”。没人能看得出,就是这群文质彬彬的客人,让欧洲大陆伏尸百万。
这些胶片拍摄于1941年夏,正是希特勒纳粹事业的巅峰,胜利似乎触手可及。
有了适合的土壤,任何国家都有可能走上同样黑暗的道路
1973年5月,贝克尔用爱娃家庭录像中的材料制作了纪录片《邪恶纳粹》,在戛纳电影节上首映。
《邪恶纳粹》塑造了一个与人们的印象完全不同的希特勒。除了私人生活中的温和、友善,影片中的希特勒也饱受民众由衷的爱戴和崇拜。
男女老少蜂拥而至,带着满脸的兴奋和激动,一心想瞻仰元首的仪容,警卫几乎无法阻止;鲜花撒在他经过的路旁;希特勒对孩子们微笑,逗一逗年轻的姑娘,给骄傲的小伙子们赞许的笑容;一位从数百人中脱颖而出,得以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担任鼓手的年轻人,看起来像是地球上最幸福的男孩。
影片中的德国人似乎无比团结和幸福,每个人都在巨大的国家机器中各得其所。他们似乎都在为理想奋斗,而不是为了金钱或是自私的目的,就连纳粹分子都面带笑容。直到影片的最后,战争、大屠杀等人们熟悉的画面才出现。
这部另类的影片迅速激起了人们的反感,甚至引发了暴力事件。这部纪录片在德国被禁了37年。
令人们不安的是,希特勒不是淌着口水的恶魔或肮脏的怪物,纳粹是与我们一般无二的人。胜利者们不愿意去想:有了适合的土壤,任何国家都有可能走上同样黑暗的道路。
这些情绪,都曾经出现在第一次看到爱娃录像的贝克尔身上。“我一直处于一种极度的兴奋中,仿佛我的生命有一种使命。我对纳粹感到愤怒,现在,我终于可以通过一种积极的方式来疏导、宣泄这些愤怒。”
如今,很多人可以以全新的视角看待第三帝国,愤怒转变为理智的审视,妖魔不再被视为妖魔,而是一个常人——即使是来自人性阴暗面的邪恶使者,也仍然是人。
对贝克尔来说,回顾爱娃的家庭录像仍然是痛苦的,人们对《邪恶纳粹》的反应也折磨着他,只不过,回顾往事,他已学会与过去和解。
“我的研究不是什么巨大的胜利,顶多是休战协议。我能够看到,过去被放进历史书里,纳粹不再像幽灵般出没。我的旅程已经结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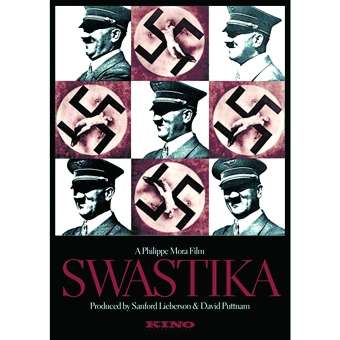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