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被告知路线时听来头头是道,旅程中的每一步显然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完全理解了。然而天黑后,就在离某地还有几英里外的荒郊野地里,我们开始争执最后一个路口是该左转还是右转,或是就地休息,并争论着这一切是谁的错。
事实上,我们没必要太难为自己。从心理上讲,指路本身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我们之所以很难指路,是源于一种叫“知识的诅咒”的心理学怪象。一旦我们学会了某事,却发现很难向未知者阐述。我们不但希望人们循着我们的足迹走,还假定他们已经知道路线。一旦我们知道了去某地的线路后,就不再需要特别的方向说明,如“走到一半左转”或者“那里有一个小红门”等此类描述就足够了。
但如果你从未去过那个地方,你需要的信息就不止是关于那个地点的描述。你需要得到明确的定义,或找到它的准确方法。“知识的诅咒”解释了,当我们在野外寻找一个朋友的帐篷时,朋友提示“帐篷是蓝色的”,这样的提示对他们自身而言似乎毋庸置疑,但对我而言毫无意义,因为我只能对着几百顶蓝色帐篷站着干瞪眼。
这种怪象同样解释了为什么教书如此困难。例如一个我们熟知的话题,我们很难明白,对于不熟悉它的人,究竟还需要知道什么。
某些场合需要我们适当考虑他人的感受和信念。指路算一例,在涉及情感、玩笑或建议的日常会话中,也需要考虑各方面因素。举个例子,某些研究认为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虽然到底怎么理解它又是另一码事):
两个猎人在丛林中,其中一人体力不支,看起来没有呼吸,眼神也呆滞了。另一个人赶紧掏出手机,呼叫紧急救援。他气喘吁吁地说:“我的朋友死了,我该怎么办?” 接线员说,“冷静一下,我来帮你。首先,我们要确认他死了”。沉寂一阵之后,接线员听到一声枪响。猎人回到电话上来,说:“好了,接下来怎么办?”
这个笑话的笑点在于,这个猎人对接线员的指示有两种潜在理解,却选了错的。要真正领悟他的理解方式,你必须觉察接线员和猎人的所知与所愿。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猎人想全力帮忙的念头太强,以致压过了他保住朋友命的念头。
想学会心理模拟,你需要应用心理学家说的“思维理论”,即思考理解他人信念和愿望的能力。思维理论上的能力,是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之一——似乎只有黑猩猩,可以趋近真正理解其他黑猩猩的不同看法。从另一方面讲,人类似乎从婴儿期就开始练习思考他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知识的诅咒”告诉我们,理解别人的思维有多难。比如看东西,人类大脑已进化出专门机制,来致力于解决此问题,故我们通常不需额外花费意志力。大多数时候我们能领会这个笑话,容易得如同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要简单睁开眼就能看到这个世界。
好消息是,“思维理论”并非完全自动的——你可以通过深思熟虑的方式,来帮助你理解别人。一个好方法是,当你写作时,你得简单要求自己检查每个词组,看看有没有术语行话——有一些你熟悉的词汇,却并不是所有读者都知道。
还有一种方法是,告诉别人哪些东西可以忽略,哪些他们需要知道。这种方法用于指路,也会有很好的效果(提示他们,如“一直走到你看到红色的门为止,还会有个一个粉红色的门,但不是你要找的”)。
借助一些诸如此类的小技巧,稍加练习,我们也许可以读懂别人的思维——有些心理学家称之为“将心比心”,将其培养成一种习惯,从而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这是件好事,因为好的思维能力会让我们成为一个考虑周全的伙伴、朋友、同事,或至少成为一个优秀的向导。
□英国广播公司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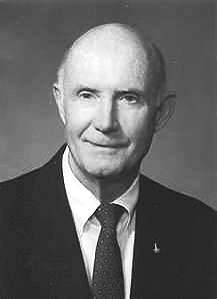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