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萨维奇路过前艳星伊薇特·维克斯的家,发现维克斯的信箱上结了厚厚的蛛网,箱内的信已经泛黄。她很好奇,难道维克斯不在家吗?这个年逾80的老太太会去哪儿?
她走过破碎的窗户,推开一扇未锁的门。屋内的情景吓了她一跳:房子里一片死寂,地上堆积着零乱的垃圾和衣服。
萨维奇紧张而好奇地走上楼。推开卧室门,彻底吓傻了:地上躺着的竟是维克斯的尸体——木乃伊般干瘪的尸体!
尸体旁的暖气片还散发着热气,电脑也仍在运行,频幕上微弱的光为这间寂寞的房间增添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
维克斯已经躺在这间屋子里大半年了。
伊薇特·维克斯的死被《洛杉矶时报》网站上一篇名为“前《花花公子》兔女郎伊薇特·维克斯的木乃伊在其家中被发现”的报道迅速传开。短短两周内,脸谱上已有16507个跟帖和 881条推讯。
萨维奇后来告诉《洛杉矶杂志》,她曾经查看了维克斯的电话账单,发现维克斯死前几个月,并没有给亲友们打过电话,而是与自己遥远的粉丝通过电话。这些粉丝是通过互联网上的粉丝团和社交网站找到她的。
这个《花花公子》前兔女郎、B级电影明星没有孩子,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也没有任何直接的社交圈子。她开始从其他地方寻找归属感。这就是社交网络。
维克斯曾经是惊悚电影的象征,她标志着好莱坞有能力以极其愚蠢的方式,调动人类最基本的恐惧;现在,她则象征着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恐怖——人类不断滋长的孤独。
这种恐怖也引发了人们更为深层的忧虑——脸谱乃至整个社交网络世界,是让我们亲密无间,还是彼此隔绝?让我们在温暖中越走越近,还是在痛苦中渐行渐远?
过去30年,科技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世界,身处其中,即使片刻间失去联系都会让人感到手足无措。
然而,就是在这个不受时空限制,能够即时、自由通讯的世界里,我们却无时无刻不被一种前所未有的疏离感折磨着——我们从未感受过彼此之间如此的疏远。
过去25年,知己(有质量的社会联系)的数量在急剧降低。一份调查显示,人们的知己数量从1985年的2.94人下降到了2004年的2.08人。1985年,只有10%的美国人认为没有朋友可以一起讨论重要的事情,15%的人表示他们只有一个这样的好朋友。到了2004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5%和20%。
其实早在脸谱出现之前,数字技术已经让我们空前地彼此隔阂。上世纪90年代,人们交往的方式开始不断增加,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接触却越来越少,学者将这种趋势称为“网络悖论”。
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文化学教授雪莉·特克于2011年出版《一起孤独》一书。她在书中质疑网络社会产生的影响:“人们希望彼此亲密,但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又很不安全,因此我们把宝押在了科技身上,也顺便寻求自我保护。”
然而,通过数字化培养起来的亲密关系终究是不完整的,互联网编织的纽带最终无法把我们连接起来。
同样,芝加哥大学认知和社会神经科学中心主任约翰·卡西奥波也认为,互联网通信带来的只是“伪”亲密。“人们与宠物、网友,甚至上帝取得联系,只是群居生物为了满足其迫切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高尚的尝试。”但社交网络这种“替代品可能永远无法完全弥补其所缺乏的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就是现实中的人,有血有肉的人。
脸谱真正“惊艳”世人的地方不是其使用人数,而是它让人们形成一种习惯,甚至是一种对脸谱的依赖。18到34岁的人群中,近半数在醒来后几分钟内,就会去脸谱上“签个到”,超过1/4起床前就会去逛逛。脸谱从不休息。我们从不休息。
伊薇特·维克斯的电脑在她死去时依然亮着。
如果我说,我想“穿越”回互联网时代来临的前夜,那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我会为此背上“矫情和忘恩负义”的骂名。
但这神奇的新机器像一个高效而优雅的服务生,甚至让我们忽视了它所不能提供的一切重要的服务。
脸谱揭示了人类天性的秘密——这可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发现——互联网并不是真正的纽带,即时、全面的通讯也不是万能的救世主,没有什么捷径能直达“美丽新世界”,直抵人类自由的灵魂深处。
过去,我们常常在孤独中“三省吾身”,并且重塑自我。但现在我们被留在大片的孤独中,有机会想想我们是谁,然而,有谁真正思考过我们到底是谁?
脸谱不可能给我们真正的快乐,因为我们低估了快乐的深刻性。那就断开连接吧,给自己一点忘我的时间!
美国《大西洋月刊》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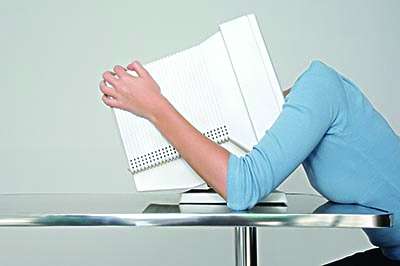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