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不只是联邦调查局的历史,它还成功地揭示并反思了公民自由和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建议我们今后如何防止历史错误重演。
在去年的电影《胡佛》中,反映这位联邦调查局老大是强硬的反犯罪斗士和异装的同性恋者的情节之比是21:2。而在新书《敌人》里,蒂姆·韦纳用半页多的篇幅告诉我们,近半个世纪来一直存在的、关于埃德加·胡佛是同性恋的传闻可能是不真实的。
“大家似乎都乐于谈论胡佛的一件丑事,那就是他和搭档克莱德·托尔森有不正当关系。很久之前,媒体就把胡佛描述成异装癖者,让公众不自觉地对他的性取向产生怀疑。”但韦纳认为,胡佛根本没有进行秘密性行为的时间,因为“他早就跟联邦调查局(FBI)结婚了”。他对工作的狂热可谓有利有弊:一方面大大加强了初创的联邦调查局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导致该局在追捕共产党员、间谍和恐怖分子过程中大量采用不正当手段,做出践踏法律的恶行。
它经常把手伸得太长
从为麦卡锡提供名单,帮助其迫害左翼人士到上世纪60年代对马丁·路德·金实施盯梢,《敌人》如实呈现了联邦调查局许多有争议的行动。韦纳通过精心铺陈情节抓住读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论点:“今天的反恐行动,其实是重复FBI早年的做法——不择手段缉拿破坏分子和间谍。过去,联邦调查局把手伸得太长,现在有时候也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联邦调查局想方设法监控“地下气象员”组织。其中一位名为比尔·戴森的探员,首次到芝加哥执行任务就被安排进行窃听。“上司让他从下午4点一直守到午夜0点,窃听学生民主会成员的谈话。”这群学生民主会成员是“地下气象员”的前身,“气象员”之说则来自鲍勃·迪伦的一句歌词,“即使没有气象员,我们也知道风往哪儿吹”。该组织对它的解读是:革命开始了,不管它往哪个方向发展,投身革命才是最紧迫的。
“地下气象员”先后策划了38次爆炸袭击,联邦调查局一次都没能抓到嫌犯,于是决定采取极端措施,允许非法监听、盗取邮件,为了对付“国家公敌”无所不用其极。目睹“地下气象员”快速发展,“戴森曾问过好些关于法律规则的问题:‘我可以在大学教室里安插线人吗?或者在整个校园里安插线人?我可以混入学生组织内部吗?我怎么办?’然而,没人嘱咐他什么规则或条例,换言之,什么都不用顾忌。”你想过吗?这些问题也是今天的FBI探员和纽约警察局的警员,在监视穆斯林社团时经常自问的。
有时候就像秘密警察
《敌人》如此引人入胜,主要原因在于它吸收了很多雪藏许久的情报资料。据说,有内部人士向韦纳提供了FBI应《信息自由法案》要求披露的数万页档案,借助这些之前从未听到、看到或提过的素材,韦纳曝光了联邦调查局在战争与和平年代不可告人的秘密。可惜,这些档案并未包括胡佛在其办公桌里保存的、“不得归档”文件袋里的东西,但允许公开的内容已足够吊人胃口,特别是1972年他去世前保存下来的、关于情报搜集活动的连续档案。
从某种意义上讲,《敌人》好比一枚时间胶囊:韦纳把官方档案、口头流传的野史和新发现的胡佛笔记糅合起来,随着一幕幕真实历史的展开,胡佛、他形形色色的部下以及他们供职的机构的完整面目陆续从迷雾中浮现。读者藉此对美国的执法力量有了新的认识。
韦纳毫不客气地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联邦调查局跟极权国家的秘密警察机构差不多。虽然它真正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几十年来屡屡藐视法律。《敌人》不只是联邦调查局的历史,和之前的《中情局罪与罚》类似,它还成功地揭示并反思了公民自由和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建议我们今后如何防止历史错误重演。
美国《华盛顿邮报》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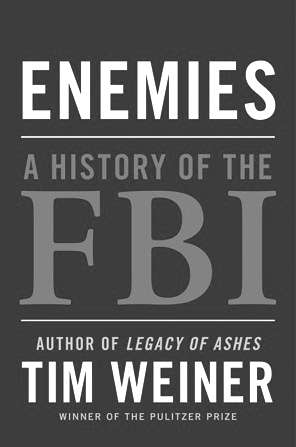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