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那次著名的中国之行的18年前,一小群英国人就踏上了这个东方大国的土地。尽管自认是西方左翼进步主义的先锋,中国东道主大呼小叫的热情款待还是让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有些困窘,有时免不了还会皱一下眉。
天安门前的另类观礼团
1954年10月的一个上午,一伙勇敢的英国旅行者目击了“可能是地球上最庞大的人群”——在5个多小时里,由男人、女人、孩子组成的洪流涌过天安门广场,庆祝新中国的生日。首先出现在广场上的是士兵、坦克和火箭发射器,然后是无尽的群众游行队伍,有人高举着列宁、斯大林和高尔基的画像,有人放飞鸽子和气球,其余的站在代表工厂和农业的彩车上向观众挥手致意。
并不是所有的西方观察家都觉得这种场面很协调,作为怀疑者之一,建筑师休·卡松爵士认为,最令人困惑的是“战士们那一张张温和的面孔”。与他一起访华的还有不少英国左翼人士,他们戴着金边眼镜,敞开的衬衫领子上别着徽章,最显眼的是每人都有一条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的领带——这是英国上流社会的标志,出现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庆祝场合显得非常不协调。在观礼台下,其他英国人在品茶,其中包括哲学家A·J·艾耶以及小说家兼诗人雷克斯·华纳。
这群英国知识分子的中国游充满了奇异的经历,成为《去往北京的护照》一书的最大亮点。作者帕特里克·赖特的笔法起初显得有点古怪,但最终会令读者忍俊不禁。
“史上最爽朗的开场白”
本书聚焦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段短暂时光,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周恩来邀请世界来看看“竹幕”后面正在发生什么。伦敦对他的邀请立即作出回应,先后派了三个代表团访华。第一个代表团由前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率领,参观了中国的工厂、学校和住宅区,毛主席也会晤过他们,并请他们喝茶。几个月之后,另一个英国代表团访问中国,成员多为比较年轻的工党议员和工会官员。
不过,真正引起赖特注意的是夹在中间那个代表团,它由地质学家列奥纳德·霍克斯牵头,上面提到的艾耶、华纳都在团里。成员中还有一位名人,那就是画家斯坦利·斯宾塞,当时是英国艺术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斯宾塞生性孤僻,一生几乎没出过老家库克汉姆村,更甭提离开英国了。当他们乘坐的飞机起飞时,他“有些发抖”,但这次访问最后还是让他的自我感觉无比良好。当被介绍给周恩来时,斯宾塞做了史上最爽朗的开场白:“你好,我就是库克汉姆村的斯坦利。”
尽管赖特的文风比较散漫,但他对斯宾塞形象的描写绝对称得上是神来之笔。这个超然物外的英国“土著”在中国参观期间,在外套下面直接穿着宽大的睡衣裤,镜片后面的眼睛眨个不停,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让导游尴尬不已。赖特在书中评论说:“即使称他为一个‘唯我主义者’,也大大低估了他的自恋程度。”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演讲时,斯宾塞称自己“可能是你们见过的最棒的访问者,可与佛教的引进相提并论。”接着,他告诉那些摸不着头脑的听众:“因为在英国,如果人们不知道我是谁,我多半会被叫去帮人搬行李。”
发现了一个新鲜的中国
从这点可以看出,赖特的书重在展示英国人在海外的表现,而非毛泽东执政早期的中国图景。他描述的重点人物,从艾德礼和他的工党同志到斯宾塞,再到代表团中其他的知识分子,大多属于作家迈克·弗雷恩笔下的“草食动物”阶级:“叛逆的中产阶级,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左翼报刊的读者,请愿书上的签名者……简而言之,他们是性情温和的反刍动物,一直生活在青葱的草原上,用悲天悯人的目光看着那些不幸的同类,对自己的优越生活有负罪感,不过他们通常也不会停止享受。”
尽管如此,代表团中的许多人还是很快发现了中国制度的特异之处,即使冷静如艾德礼也改变了自己的成见——要知道,他一直是坚定的反共分子,也是北约的创始人之一。艾德礼回国后在工党会议上说:“拥有伟大传统的中国人决不会迷恋共产主义的初级形式。”
要说本书最出彩的部分,要数每个英国人带回本国的新鲜思考方式。看到中国刚刚兴起的合作社后,这个工党代表团的成员立即将其与英国的合作社加以比较;插画家保罗·贺加斯则认为,乘火车到上海就好像“从谢菲尔德到曼彻斯特”。
尤其特别的是斯宾塞的评论。当周恩来说英国应该更好地了解新中国时,斯宾塞的回答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孤傲和偏狭,他一本正经地强调:“是的,你们也应该更好地了解库克汉姆村。我在中国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因为库克汉姆似乎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显然,斯宾塞当时并未意识到大英帝国的衰落,也对剧烈变化的世界格局缺乏认知。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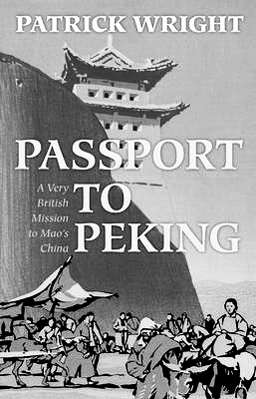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