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智库观察
(3月28日至4月4日)
综合编译 袁野
来源:青年参考
(2025年04月04日 04版)
《美国政治学杂志》:公众对人工智能与全球化的态度及其政治影响

人工智能被视为与全球化并列的两大关键变革力量,两者都会在多个维度(就业、生产率、价格)产生复杂的经济效应,包括创造就业机会、降低价格及工作岗位流失。人工智能是否会像全球化一样挑战现有模式并引发政治反弹?《美国政治学杂志》研究了公众对作为全球化典型表现的离岸外包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态度差异,重点关注公众在就业变化和价格变化间的权衡。文章选取美国和加拿大的6000名受访者进行联合调查,研究发现:(1)公众对价格变化的敏感度不亚于甚至超过就业变化;在就业变化维度内,公众对AI造成的失业比AI创造的就业更敏感。(2)公众对AI的支持度总体高于离岸外包,美国民主党人尤为乐观,共和党人与加拿大人更谨慎。(3)政治党派影响显著:美国两党对离岸外包的态度呈明显分化;AI尚未被政治化,但有潜在党派分歧风险。
总而言之,AI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力方面有巨大潜力,但公众对工作岗位转移和不平等的担忧值得关注。如果不加以控制,AI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并进一步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主导企业手中。
作者贝阿特丽斯·玛吉斯特罗(Beatrice Magistro)是加州理工学院人文与社科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研究兴趣为政治经济学与政治行为学。
《布鲁塞尔信号》:欧洲和美国会“离婚”吗

美欧关系似乎已经陷入二战以来最紧张的时刻。比利时《布鲁塞尔信号》杂志刊发文章,试图回答一个世人关心的问题:欧洲和美国会“离婚”吗?作者梳理欧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与当前困境,分析指出: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自二战后建立,宣称基于共同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但起初更多是出于对抗苏联的共同利益。冷战结束后,双方关系因利益与价值观的交织而得以延续,但分歧不断涌现——美国要求欧洲服从其全球战略,欧洲则拒绝为美国利益牺牲自己的优先事项。
作者认为,“离婚”隐喻虽反映了当前的紧张关系,但真正“分手”将带来灾难,美欧在利益与价值观上仍有交集。欧洲若能清醒认识到综合国力竞争的现实,就有与美国协商调整关系的空间,也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升话语权;美国若改变一些固有思维,双方也可能构建基于务实合作的新型关系。
作者亨利·奥尔森(Henry Olsen)是美国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的研究员,他研究并发表有关美国政治的评论。他的工作重点在于探讨美国的政治秩序如何因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挑战而受到冲击。
斯特凡·沃尔夫:特朗普关于美中俄世界新秩序的愿景

国际问题专家斯特凡·沃尔夫近日在香港《亚洲时报》发文分析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力于促进俄乌冲突的和平解决,但他不会一味迁就俄罗斯总统普京,甚至不会在乌克兰问题上安抚普京。沃尔夫认为,特朗普有一个美中俄世界新秩序的愿景,他要将国际体系重塑,以符合19世纪思维的世界观。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美国将回归“光荣孤立”状态,在西半球保持绝对主导地位,同时在欧亚大陆构建互不干涉的势力范围。
沃尔夫称,离间中俄或许是特朗普团队的一厢情愿,现实是俄罗斯依赖中国,而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这种三角关系绝非简单的交易所能瓦解。当俄罗斯在战略上需要中国的支持,当中国在科技领域必须突破美国的封锁,任何试图割裂中俄的企图,都将在地缘现实的面前碰得粉碎。如果美国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达成协议,那么特朗普所能实现的只是美国进一步收缩到西半球。这将使俄罗斯和中国不受美国的阻碍。
斯特凡·沃尔夫(Stefan Wolff)是德国政治学家、英国伯明翰大学国际安全教授。他是国际安全方面的专家,尤其是在管理、解决和预防种族冲突方面。
美国前贸易代表:美加200年同盟为何走到破裂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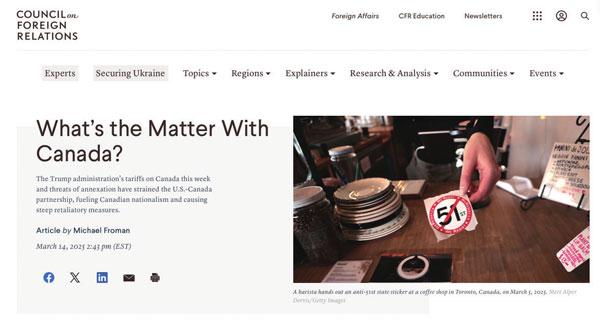
近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刊发该机构主席迈克尔·弗罗曼的文章,探讨关税战背后的北美裂变。文章称,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基石正在遭遇1979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来最严峻挑战。美加矛盾已超越传统贸易摩擦范畴,演变为规则体系与战略互信的全面危机。当五眼联盟与北美防空司令部等“压舱石”机制被纳入博弈棋盘,这场危机不仅考验拜登时代留下的同盟管理遗产,更将重塑全球化退潮下的地缘经济格局。然而,美国承受不起合作破裂的代价。
作者迈克尔·弗罗曼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他是美国前贸易代表,也是万事达公司的副主席兼负责战略增长事务的总裁。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如何破解“外援”困局

特朗普政府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并入美国国务院的改革,标志着美国对外援助体系启动近60年来最激进的结构调整。此举旨在通过“全政府协同”机制,将年均350亿美元的外援预算转化为对抗中国影响力的战略工具。这场合并面临三重悖论:技术官僚流失(仅20%项目保留)、“国会指定支出”僵局(国会对外援助预算中,60%的资金只能用于人道主义和卫生援助)、发展援助与地缘博弈的深层张力。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文章称,从全球发展治理视角看,美国此举折射出三大趋势:一是援助武器化,效仿英国、澳大利亚模式,将发展资金纳入“大国竞争”工具箱;二是规则重构:通过DFC(开发金融公司)扩容千亿美元信贷能力,打造“美元基建”,与“一带一路”竞争;三是技术脱钩:以区块链追踪、AI评估等数字化手段,将援助数据纳入对华技术遏制网络。
作者丹尼尔·F·伦德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加入该机构之前,他曾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世界银行集团担任领导职务。
新“灰色地带”:美国如何通过出口管制服务其地缘经济战略

当前,学术界将中美竞争定义为“争夺基础设施、数字、生产和金融网络中心地位的竞争”,在针对各类国际网络的竞争中,美国将出口管制作为维护其国家安全和竞争领先地位的工具。2018年出台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赋予美国总统广泛的权力,能够对军民两用物品实施出口管制。ECRA保留了原有的美国出口管制法规,同时收紧了对管制物品的限制条款,扩大了管制物品的范围,将“新兴和基础技术”纳入其中。
美国《太平洋评论》刊发文章,研究了美国将出口管制与产业政策相结合,开展新的地缘经济战略的现象。文章认为,美国越来越多地将出口管制用作地缘经济工具来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以半导体行业为代表。在此过程中,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BIS)逐渐成为关键机构。文章认为,通过阻止中国获取关键技术,美国试图巩固自身的国际领导地位,但也会造成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的长期分裂,引发国际经济治理问题。
作者吉列尔姆·施奈德·拉萨多尔(Guilherme Schneider Rasador)是巴西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国际战略研究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和地缘经济学;作者安德鲁·莫雷拉·库尼亚(André Moreira Cunha)是巴西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经济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文化和创意经济学。
责任编辑:张昊天
来源:青年参考
2025年04月04日 04版
《美国政治学杂志》:公众对人工智能与全球化的态度及其政治影响

人工智能被视为与全球化并列的两大关键变革力量,两者都会在多个维度(就业、生产率、价格)产生复杂的经济效应,包括创造就业机会、降低价格及工作岗位流失。人工智能是否会像全球化一样挑战现有模式并引发政治反弹?《美国政治学杂志》研究了公众对作为全球化典型表现的离岸外包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态度差异,重点关注公众在就业变化和价格变化间的权衡。文章选取美国和加拿大的6000名受访者进行联合调查,研究发现:(1)公众对价格变化的敏感度不亚于甚至超过就业变化;在就业变化维度内,公众对AI造成的失业比AI创造的就业更敏感。(2)公众对AI的支持度总体高于离岸外包,美国民主党人尤为乐观,共和党人与加拿大人更谨慎。(3)政治党派影响显著:美国两党对离岸外包的态度呈明显分化;AI尚未被政治化,但有潜在党派分歧风险。
总而言之,AI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力方面有巨大潜力,但公众对工作岗位转移和不平等的担忧值得关注。如果不加以控制,AI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并进一步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主导企业手中。
作者贝阿特丽斯·玛吉斯特罗(Beatrice Magistro)是加州理工学院人文与社科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研究兴趣为政治经济学与政治行为学。
《布鲁塞尔信号》:欧洲和美国会“离婚”吗

美欧关系似乎已经陷入二战以来最紧张的时刻。比利时《布鲁塞尔信号》杂志刊发文章,试图回答一个世人关心的问题:欧洲和美国会“离婚”吗?作者梳理欧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与当前困境,分析指出: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自二战后建立,宣称基于共同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但起初更多是出于对抗苏联的共同利益。冷战结束后,双方关系因利益与价值观的交织而得以延续,但分歧不断涌现——美国要求欧洲服从其全球战略,欧洲则拒绝为美国利益牺牲自己的优先事项。
作者认为,“离婚”隐喻虽反映了当前的紧张关系,但真正“分手”将带来灾难,美欧在利益与价值观上仍有交集。欧洲若能清醒认识到综合国力竞争的现实,就有与美国协商调整关系的空间,也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升话语权;美国若改变一些固有思维,双方也可能构建基于务实合作的新型关系。
作者亨利·奥尔森(Henry Olsen)是美国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的研究员,他研究并发表有关美国政治的评论。他的工作重点在于探讨美国的政治秩序如何因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挑战而受到冲击。
斯特凡·沃尔夫:特朗普关于美中俄世界新秩序的愿景

国际问题专家斯特凡·沃尔夫近日在香港《亚洲时报》发文分析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力于促进俄乌冲突的和平解决,但他不会一味迁就俄罗斯总统普京,甚至不会在乌克兰问题上安抚普京。沃尔夫认为,特朗普有一个美中俄世界新秩序的愿景,他要将国际体系重塑,以符合19世纪思维的世界观。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美国将回归“光荣孤立”状态,在西半球保持绝对主导地位,同时在欧亚大陆构建互不干涉的势力范围。
沃尔夫称,离间中俄或许是特朗普团队的一厢情愿,现实是俄罗斯依赖中国,而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这种三角关系绝非简单的交易所能瓦解。当俄罗斯在战略上需要中国的支持,当中国在科技领域必须突破美国的封锁,任何试图割裂中俄的企图,都将在地缘现实的面前碰得粉碎。如果美国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达成协议,那么特朗普所能实现的只是美国进一步收缩到西半球。这将使俄罗斯和中国不受美国的阻碍。
斯特凡·沃尔夫(Stefan Wolff)是德国政治学家、英国伯明翰大学国际安全教授。他是国际安全方面的专家,尤其是在管理、解决和预防种族冲突方面。
美国前贸易代表:美加200年同盟为何走到破裂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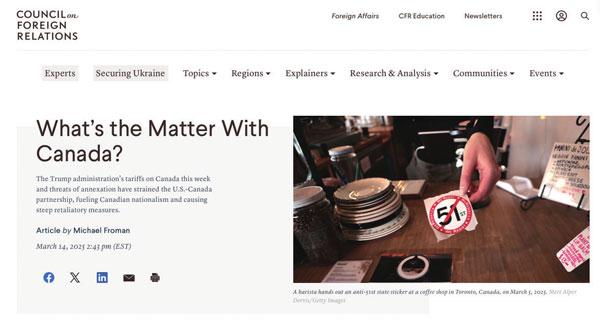
近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刊发该机构主席迈克尔·弗罗曼的文章,探讨关税战背后的北美裂变。文章称,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基石正在遭遇1979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来最严峻挑战。美加矛盾已超越传统贸易摩擦范畴,演变为规则体系与战略互信的全面危机。当五眼联盟与北美防空司令部等“压舱石”机制被纳入博弈棋盘,这场危机不仅考验拜登时代留下的同盟管理遗产,更将重塑全球化退潮下的地缘经济格局。然而,美国承受不起合作破裂的代价。
作者迈克尔·弗罗曼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他是美国前贸易代表,也是万事达公司的副主席兼负责战略增长事务的总裁。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如何破解“外援”困局

特朗普政府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并入美国国务院的改革,标志着美国对外援助体系启动近60年来最激进的结构调整。此举旨在通过“全政府协同”机制,将年均350亿美元的外援预算转化为对抗中国影响力的战略工具。这场合并面临三重悖论:技术官僚流失(仅20%项目保留)、“国会指定支出”僵局(国会对外援助预算中,60%的资金只能用于人道主义和卫生援助)、发展援助与地缘博弈的深层张力。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文章称,从全球发展治理视角看,美国此举折射出三大趋势:一是援助武器化,效仿英国、澳大利亚模式,将发展资金纳入“大国竞争”工具箱;二是规则重构:通过DFC(开发金融公司)扩容千亿美元信贷能力,打造“美元基建”,与“一带一路”竞争;三是技术脱钩:以区块链追踪、AI评估等数字化手段,将援助数据纳入对华技术遏制网络。
作者丹尼尔·F·伦德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加入该机构之前,他曾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世界银行集团担任领导职务。
新“灰色地带”:美国如何通过出口管制服务其地缘经济战略

当前,学术界将中美竞争定义为“争夺基础设施、数字、生产和金融网络中心地位的竞争”,在针对各类国际网络的竞争中,美国将出口管制作为维护其国家安全和竞争领先地位的工具。2018年出台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赋予美国总统广泛的权力,能够对军民两用物品实施出口管制。ECRA保留了原有的美国出口管制法规,同时收紧了对管制物品的限制条款,扩大了管制物品的范围,将“新兴和基础技术”纳入其中。
美国《太平洋评论》刊发文章,研究了美国将出口管制与产业政策相结合,开展新的地缘经济战略的现象。文章认为,美国越来越多地将出口管制用作地缘经济工具来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以半导体行业为代表。在此过程中,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BIS)逐渐成为关键机构。文章认为,通过阻止中国获取关键技术,美国试图巩固自身的国际领导地位,但也会造成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的长期分裂,引发国际经济治理问题。
作者吉列尔姆·施奈德·拉萨多尔(Guilherme Schneider Rasador)是巴西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国际战略研究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和地缘经济学;作者安德鲁·莫雷拉·库尼亚(André Moreira Cunha)是巴西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经济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文化和创意经济学。
责任编辑:张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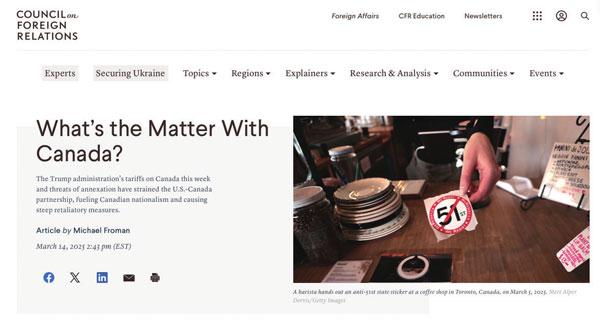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