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里,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裂痕已扩大为峡谷,越来越多的财富被新生精英阶层占有。这些富人如何发迹、怎样生活,又通过什么方式拓展其影响力?
古往今来最有钱的人是谁?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就像战车与飞机无法比较火力。但是,仍然有一位经济学家力图给出回答,即用亚当·斯密率先提出的一种通用测算方法,其基础是年收入相当于公民平均工资的倍数。
获胜者不是马库斯·克拉苏,尽管他的财富等同于罗马帝国的国库,回报率却是微不足道的;也不是镀金时代的“传奇大亨”安德鲁·卡内基,他的财富于1901年达到了顶峰,每年捧回家的美元等于48000名普通美国人的收入;那约翰·洛克菲勒呢?这个石油巨头干一年的收入,约等于他手下一名普通工人连续劳动11.6万年积累的总和。
与自命不凡的华尔街金融家、靠创意来钱的硅谷亿万富翁以及那些掠夺了俄罗斯的寡头相比,这些历史人物相形见绌。在21世纪,墨西哥电信业霸主卡洛斯·斯利姆一人就盖过他们全部,斯利姆的财富达530亿英镑,与其同胞的年收入比值达400000:1。
国籍已非他们的身份符号
这回,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在新书《富豪们》中要谈的,不是所谓1%,而是0.1%。大概是担心读者没有概念,她特别引用了另一组足以令人震惊和不安的对比数据:30年前,美国总裁的平均收入是雇员平均收入的42倍,今天,这个比率已经达到了可憎的380倍——而且你还要记住,前一类人越是富有,需要交纳的所得税占总体比例就越小,更不用提种种暗藏机关的避税秘诀。
尽管本书的封面装帧有点俗气,尽管有流言说作者通过与明星开派对获得了100万美元的赞助费,它绝不止于对富人和名人的私生活进行浅薄的窥探。弗里兰试图研究全球趋势,探索这么多“钱堆起来的精英”的社会影响力,用图表显示这个阶层的崛起,毫不突兀地从大量的学术研究和对乔治·索罗斯的采访,转换到Lady Gaga的成功之道上去。
那么,这些富豪是些怎样的家伙呢?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的钱大多是自己挣来的,而非来自继承。另一重共性在于,他们多数是“外来者”,如带有犹太血统的俄罗斯寡头,足够聪明、也有足够的动力在苏联体制崩溃的过程中渔利。毫无疑问,银行家和金融家主导着这个俱乐部,随后才是那些技术巨头;另外,为这部分人提供服务的律师甚至牙医也有机会加入他们的行列。“超级明星为超级富豪工作,收取超级费用。”弗里兰戏谑地写道。
她的发现根植于细致的研究、高效的统计和齐整而有价值的信息。《富豪们》指出,技术扩散和全球化在很多行业创造出赢者通吃的文化,使成功人士加入一个超国界的大共同体。这些人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参加相同的派对,享受相同的服务。事实上,富豪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多于他们与本国同胞的共同点,无论他们来自非洲、亚洲还是西方。
无邪恶动机 却有负面影响
当然,有钱人的私生活未必美满。为获得财富,家庭往往成为牺牲品。一位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花在旅途中的总裁可怜兮兮地表示:“我对空中小姐的了解比妻子更深。”
与普罗大众的隔离也容易催生傲慢情绪。“如果一个人不想当寡头,他肯定有病。”被普京投入监狱前,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曾如此扬言。的确,巨额财富和猖獗的利己主义可以混合出“易燃物”,在中国,过去10年里,有14位亿万富翁引火烧身,被判处死刑。
我们不能期待这本小书提出解决贫富差距的良方。弗里兰只是警告:当一个自我服务和自我满足的小团体主宰公共话语权,并寻求更倾向于保护其利益的体制时,就会带来巨大危险。不过,这些精英分子并非天生邪恶,而是真诚地相信:对他们好的,对大家都有益。
讽刺性的结局是,本该代表公益的政府往往成为富豪最好的朋友——无论是在国家资本主义的东方,还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的欧美。金融危机表明,人才都是跟着钱走的,因此,“仅从银行家的巨额收入中分得一点残渣的监管者,根本不是这些全球性巨兽的对手”。
这些亿万富翁明面上赞扬自由市场价值观,背地里却大力游说而且经常成功地让市场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从而“削弱了传统的中产阶级,扰乱了社会的流动性”。然而,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这样做,也是在逐步摧毁曾经孕育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外部环境。
英国《卫报》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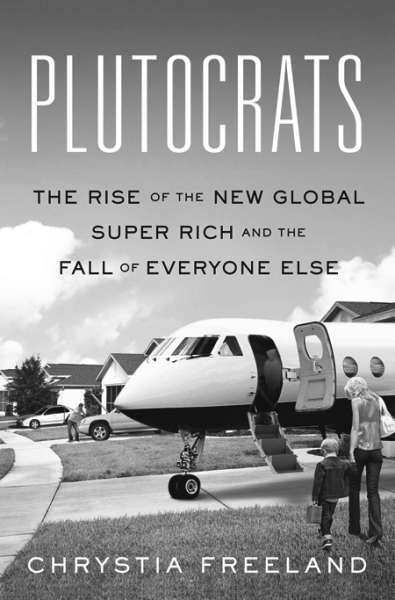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