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番茄炒蛋般实在的中德爱情
———走出国门寻找爱(一)
本报特约撰稿 叶莹
《
青年参考
》(
2015年05月13日
10
版)
 |
越过千山万水,一段中德跨国恋情终于开花结果。(▋图片由作者提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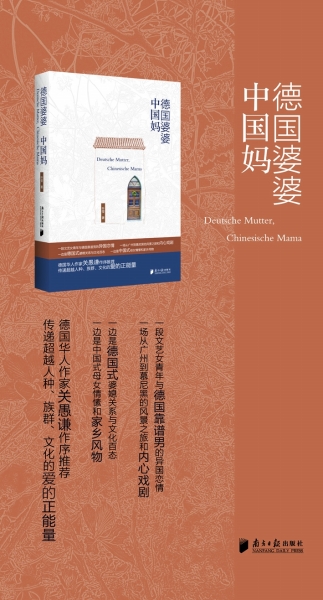 |
本文节选自叶莹的长篇纪实小说《德国婆婆中国妈》。5月17日下午,该书作者将在北京市海淀图书城言几又书店举行新书签售会。 |
女大当嫁
母亲掏出钥匙,打开厚重的防盗铁门走进来,她把手中那把桂林山水墨画纸扇折叠起来,脸上焕发着有点异样的光彩。看见正坐在客厅沙发椅上看电视的我,她扭动着秧歌般的轻盈步伐旋转到我身边。
“鑫,我今晚在小区花园运动时又碰见宁阿姨。”母亲的声调里充满难以抑制的兴奋。
“宁阿姨在广州可没儿子呀!”我头也不抬,敷衍着母亲。电视里正播放着介绍黄山风景的纪录片。
“她有个女儿思诗,准备去德国留学了。”母亲又打开手中折扇,这套面北的房子很是闷热。我一心想着“五一”黄金周快到了,是否这次带父母去游一趟黄山呢。
“你想不想也去出国留学呢,女儿?”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以为听到的声音是从电视里传出的。可是电视屏幕上仍是解说员声情并茂的黄山风景赞美词。我直盯着母亲蠕动的嘴巴有些晃神,但她嘴里吐出来的字却很清晰:“我是想着,中国很多优秀的男孩子都跑到外国去了,你在外面可能还更容易找到合适的。”
我把电视关上。
大学毕业六七年了,可是母亲盼望的“准女婿”还不出现。心急的她借口我上班辛苦,要来我身边小住一阵子,为我做饭煲汤。只是喝了几个星期母亲的汤后,我渐渐发现了她的醉翁之意不在酒。
母亲每天早上都到小区花园里打太极。她说那里的老人信息可灵通了,都知道谁家有儿未娶哪家有女未嫁。有时候,她会抄回来一堆名字和电话号码,然后问我有兴趣和谁见面。
但是今天,她竟然问我想不想出国。我一时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回答她。
我给男闺蜜大翔拨了电话,相约一起在江边的周记大排档吃晚饭。
当我把妈妈的愿望告诉他时,他鼓起双目,嘴巴定格在一个大圆形上。我笑开了:“我知道你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你比我还更了解我母亲对我的依恋。但是她认为,我出去了,会把幸福带回来。”
“鑫,是的。我了解你,你对母亲的依恋也绝对不比她对你的少。但如果有机会,你就去德国吧。直觉告诉我,那会是你走对的路。”大翔以最霸道的方式结束了我的左右为难。
柏林,柏林
柏林特格尔机场很小,和我想象中豪华气派的国际大都市机场相差甚远。
到达柏林的第二天,思诗便带我坐地铁去柏林蒂尔加滕中心公园参加“爱情大游行”。这天天气极好,天空的那抹湛蓝把拥挤的人群染成一片蓝色海洋。我紧拉思诗的衣角,在这片疯狂的海洋里任凭自己浪起浪落。
思诗则举着她的柯达大相机,“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一对上身袒露,染着红毛绿发的小伙子从我身旁经过,看见思诗手中的相机,他们马上揽住我肩膀,对着镜头搔首弄姿一番。从他们身上飘来的浓郁香奈尔香水味,让我有种晕船的迷惘。我想抬头张望蓝天,却瞥见路边的电线杆,也成了人们向世界宣爱的制高点。
我被这场能让爱的能量无止境释放的大游行吸引,尽情感受着那些自由天空下奔放的灵魂与疯狂的躯体。走向归途时,思诗还在兴奋地盘点着今天镜头的收获,待心中的狂热慢慢恢复平静后,我回望中心公园的那座金色凯旋柱,对思诗轻叹:“德国人真好,可以这般放纵自己。但是我想象不出,我以后会找一个德国男朋友。”我的脑际又掠过了那袒露着茸茸黄毛的胸膛,刺鼻的香水味,还有像公鸡尾巴般多彩的发式,然后坚决地对自己摇了摇头。
思诗赶忙用手指顶着双唇“嘘”了一声。她说:“这些话不能说,一说就破。”
我怔了一下,赶快补充:“万一真被我说破了,我不小心找了个德国男朋友的话,那么他不能打扮得这么奇形怪状的,而且他要能跟我回中国去。”
思诗这回低下了头,幽幽地回了我一句:“如果爱情能让人规划的话,便不会有今天这个大游行了。”
番茄炒蛋式的求婚
这是我来到因城大学的第一个夏天。因城是一座位于德国东南部多瑙河岸的小城。一到艳阳高照的日子,这里便举办夏季联欢节。联欢节持续数日,规模宏大,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民间表演队,更有各式特色摊位助兴,大有一城欢庆、百方客至之壮观。
联欢节的最后一天,我站在古城堡的大门口,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卖印度饰物的小摊看。我喜欢上那个五颜六色的小布包,但被上面的标价吓住了。这在犹豫徘徊之际,我耳边传来一个男中音说出的中文:“你好!”我略微抬头,看到一件格子衬衫上的领口。
我继续把头扬起,便看见了一张长长的脸。长脸还特别配个板寸,脸更显得离奇的长了。长脸的高鼻梁上,架着一副与脸的长度不成比例的小圆片眼镜。镜片后透出的目光,有点像刚从多瑙河里出来的鸭子背,亮堂堂的很澄净。
他把手向我伸过来:“你好!我是爱德华。”声调全部是第二声。我也把手伸出去:“你好!我是鑫。”
他继续开口说话,变成了德语。他说,他去年去了中国很多地方,中国太好玩了,中国菜太好吃了。说到最后我也兴奋不已,跟着他穿过古城堡的拱门走到河边公园。路过卖雪糕的摊档时,他仿佛忘了刚才赞不绝口的北京锅贴西安泡馍,低头轻声问我:“我们吃雪糕好不好?”
他要了两个雪糕,把一个塞我手中。我说我不爱吃雪糕。他像是看到了怪物似的一声惊叹: “是吗?!”不过他马上又说:“那你先拿着它,我吃完了再继续帮你吃。”然后他的右手牵起了我的左手。我浑身紧张,我说在中国第一次见面男孩子不会拉女孩子手的。他说,在德国他拉才认识了半个小时的女孩的手,也是第一次。
我们坐在一张长椅子上开始聊天,他主动说自己在慕尼黑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工作。我对他略表敬意:造飞机呀,多了不起!他马上补充,他不是造飞机的工程师,他是给造飞机的人管好财税而已。但是这家公司现正在申请破产,他一年后也要重新去找工作了。
德国那阵子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很多大企业都因为竞争能力的缺乏而相继关门。德国的失业大军高达四百多万,差不多百分之十的失业率。有人埋怨全球化是祸首,让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抢走了老牌工业大国的饭碗。
但是这个面临加入失业大军的爱德华,好像对我这个来自新兴国家的潜在威胁者毫无怨气。相反,他很热情地在临走时给我留下了联系地址,当然也没忘记索取我的。
一个月后,我第一次到他在慕尼黑的住所作客。晚饭时,他从厨拿出一大堆东西招待我:面包、奶酪、番茄、香肠……而拥有中国胃的我看着这些就想逃跑。
“你有没有鸡蛋?”我问他,然后做了一盘番茄炒蛋。没想到,这酸酸甜甜的一盘番茄炒蛋拉开了我们的爱情序幕。爱德华吃了一口后便不能自已,他一边啧啧称赞,一边用面包把盘里最后一点番茄汁抹得干干净净。
这年冬天,德国飘起了很大的雪。一个周日,我们在银装素裹的树林里散步。我跟他说起,自己准备在寒假回国看望父母的事。他有点紧张地问:“可不可以让我陪你一起去?”
还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你还有一年就毕业,我想在你的学生签证到期前和你结婚。所以,我要去向你的父母提亲。你知道,在德国,像我们这样的跨国婚姻,手续特繁琐。”
我说我们才认识半年啊!他却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说以前没人告诉他番茄炒蛋会这么好吃,所以他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做番茄炒蛋的人。
我半响答不上话来:从15岁开始看文艺爱情片,我能想象到的浪漫求婚镜头不下千百个,但绝对不会有像爱德华这般,像在吃着一盘番茄炒蛋般的实在。
突然之间,我意识到,做番茄炒蛋,也需要一个好锅啊。我没忘记,快要加入“失业大军”的他……
待他从我扭扭捏捏的套话里明白我的担忧时,却像孩子般发出爽朗却有力的笑声:我才三十多岁,这么年轻,怎么会害怕找不到工作呢?
我把自己的脸深深地埋进他怀抱,再也不愿意离开。我相信着,用这样懂得生活真义的乐观态度支撑出来的日子,不会坏到哪里去的。
女大当嫁
母亲掏出钥匙,打开厚重的防盗铁门走进来,她把手中那把桂林山水墨画纸扇折叠起来,脸上焕发着有点异样的光彩。看见正坐在客厅沙发椅上看电视的我,她扭动着秧歌般的轻盈步伐旋转到我身边。
“鑫,我今晚在小区花园运动时又碰见宁阿姨。”母亲的声调里充满难以抑制的兴奋。
“宁阿姨在广州可没儿子呀!”我头也不抬,敷衍着母亲。电视里正播放着介绍黄山风景的纪录片。
“她有个女儿思诗,准备去德国留学了。”母亲又打开手中折扇,这套面北的房子很是闷热。我一心想着“五一”黄金周快到了,是否这次带父母去游一趟黄山呢。
“你想不想也去出国留学呢,女儿?”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以为听到的声音是从电视里传出的。可是电视屏幕上仍是解说员声情并茂的黄山风景赞美词。我直盯着母亲蠕动的嘴巴有些晃神,但她嘴里吐出来的字却很清晰:“我是想着,中国很多优秀的男孩子都跑到外国去了,你在外面可能还更容易找到合适的。”
我把电视关上。
大学毕业六七年了,可是母亲盼望的“准女婿”还不出现。心急的她借口我上班辛苦,要来我身边小住一阵子,为我做饭煲汤。只是喝了几个星期母亲的汤后,我渐渐发现了她的醉翁之意不在酒。
母亲每天早上都到小区花园里打太极。她说那里的老人信息可灵通了,都知道谁家有儿未娶哪家有女未嫁。有时候,她会抄回来一堆名字和电话号码,然后问我有兴趣和谁见面。
但是今天,她竟然问我想不想出国。我一时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回答她。
我给男闺蜜大翔拨了电话,相约一起在江边的周记大排档吃晚饭。
当我把妈妈的愿望告诉他时,他鼓起双目,嘴巴定格在一个大圆形上。我笑开了:“我知道你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你比我还更了解我母亲对我的依恋。但是她认为,我出去了,会把幸福带回来。”
“鑫,是的。我了解你,你对母亲的依恋也绝对不比她对你的少。但如果有机会,你就去德国吧。直觉告诉我,那会是你走对的路。”大翔以最霸道的方式结束了我的左右为难。
柏林,柏林
柏林特格尔机场很小,和我想象中豪华气派的国际大都市机场相差甚远。
到达柏林的第二天,思诗便带我坐地铁去柏林蒂尔加滕中心公园参加“爱情大游行”。这天天气极好,天空的那抹湛蓝把拥挤的人群染成一片蓝色海洋。我紧拉思诗的衣角,在这片疯狂的海洋里任凭自己浪起浪落。
思诗则举着她的柯达大相机,“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一对上身袒露,染着红毛绿发的小伙子从我身旁经过,看见思诗手中的相机,他们马上揽住我肩膀,对着镜头搔首弄姿一番。从他们身上飘来的浓郁香奈尔香水味,让我有种晕船的迷惘。我想抬头张望蓝天,却瞥见路边的电线杆,也成了人们向世界宣爱的制高点。
我被这场能让爱的能量无止境释放的大游行吸引,尽情感受着那些自由天空下奔放的灵魂与疯狂的躯体。走向归途时,思诗还在兴奋地盘点着今天镜头的收获,待心中的狂热慢慢恢复平静后,我回望中心公园的那座金色凯旋柱,对思诗轻叹:“德国人真好,可以这般放纵自己。但是我想象不出,我以后会找一个德国男朋友。”我的脑际又掠过了那袒露着茸茸黄毛的胸膛,刺鼻的香水味,还有像公鸡尾巴般多彩的发式,然后坚决地对自己摇了摇头。
思诗赶忙用手指顶着双唇“嘘”了一声。她说:“这些话不能说,一说就破。”
我怔了一下,赶快补充:“万一真被我说破了,我不小心找了个德国男朋友的话,那么他不能打扮得这么奇形怪状的,而且他要能跟我回中国去。”
思诗这回低下了头,幽幽地回了我一句:“如果爱情能让人规划的话,便不会有今天这个大游行了。”
番茄炒蛋式的求婚
这是我来到因城大学的第一个夏天。因城是一座位于德国东南部多瑙河岸的小城。一到艳阳高照的日子,这里便举办夏季联欢节。联欢节持续数日,规模宏大,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民间表演队,更有各式特色摊位助兴,大有一城欢庆、百方客至之壮观。
联欢节的最后一天,我站在古城堡的大门口,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卖印度饰物的小摊看。我喜欢上那个五颜六色的小布包,但被上面的标价吓住了。这在犹豫徘徊之际,我耳边传来一个男中音说出的中文:“你好!”我略微抬头,看到一件格子衬衫上的领口。
我继续把头扬起,便看见了一张长长的脸。长脸还特别配个板寸,脸更显得离奇的长了。长脸的高鼻梁上,架着一副与脸的长度不成比例的小圆片眼镜。镜片后透出的目光,有点像刚从多瑙河里出来的鸭子背,亮堂堂的很澄净。
他把手向我伸过来:“你好!我是爱德华。”声调全部是第二声。我也把手伸出去:“你好!我是鑫。”
他继续开口说话,变成了德语。他说,他去年去了中国很多地方,中国太好玩了,中国菜太好吃了。说到最后我也兴奋不已,跟着他穿过古城堡的拱门走到河边公园。路过卖雪糕的摊档时,他仿佛忘了刚才赞不绝口的北京锅贴西安泡馍,低头轻声问我:“我们吃雪糕好不好?”
他要了两个雪糕,把一个塞我手中。我说我不爱吃雪糕。他像是看到了怪物似的一声惊叹: “是吗?!”不过他马上又说:“那你先拿着它,我吃完了再继续帮你吃。”然后他的右手牵起了我的左手。我浑身紧张,我说在中国第一次见面男孩子不会拉女孩子手的。他说,在德国他拉才认识了半个小时的女孩的手,也是第一次。
我们坐在一张长椅子上开始聊天,他主动说自己在慕尼黑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工作。我对他略表敬意:造飞机呀,多了不起!他马上补充,他不是造飞机的工程师,他是给造飞机的人管好财税而已。但是这家公司现正在申请破产,他一年后也要重新去找工作了。
德国那阵子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很多大企业都因为竞争能力的缺乏而相继关门。德国的失业大军高达四百多万,差不多百分之十的失业率。有人埋怨全球化是祸首,让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抢走了老牌工业大国的饭碗。
但是这个面临加入失业大军的爱德华,好像对我这个来自新兴国家的潜在威胁者毫无怨气。相反,他很热情地在临走时给我留下了联系地址,当然也没忘记索取我的。
一个月后,我第一次到他在慕尼黑的住所作客。晚饭时,他从厨拿出一大堆东西招待我:面包、奶酪、番茄、香肠……而拥有中国胃的我看着这些就想逃跑。
“你有没有鸡蛋?”我问他,然后做了一盘番茄炒蛋。没想到,这酸酸甜甜的一盘番茄炒蛋拉开了我们的爱情序幕。爱德华吃了一口后便不能自已,他一边啧啧称赞,一边用面包把盘里最后一点番茄汁抹得干干净净。
这年冬天,德国飘起了很大的雪。一个周日,我们在银装素裹的树林里散步。我跟他说起,自己准备在寒假回国看望父母的事。他有点紧张地问:“可不可以让我陪你一起去?”
还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你还有一年就毕业,我想在你的学生签证到期前和你结婚。所以,我要去向你的父母提亲。你知道,在德国,像我们这样的跨国婚姻,手续特繁琐。”
我说我们才认识半年啊!他却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说以前没人告诉他番茄炒蛋会这么好吃,所以他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做番茄炒蛋的人。
我半响答不上话来:从15岁开始看文艺爱情片,我能想象到的浪漫求婚镜头不下千百个,但绝对不会有像爱德华这般,像在吃着一盘番茄炒蛋般的实在。
突然之间,我意识到,做番茄炒蛋,也需要一个好锅啊。我没忘记,快要加入“失业大军”的他……
待他从我扭扭捏捏的套话里明白我的担忧时,却像孩子般发出爽朗却有力的笑声:我才三十多岁,这么年轻,怎么会害怕找不到工作呢?
我把自己的脸深深地埋进他怀抱,再也不愿意离开。我相信着,用这样懂得生活真义的乐观态度支撑出来的日子,不会坏到哪里去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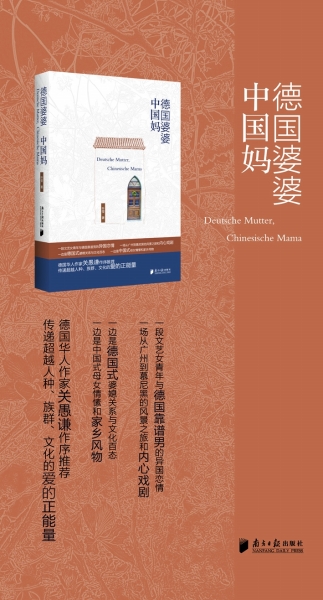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