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还是英国语?
李龑
《
青年参考
》(
2015年04月01日
10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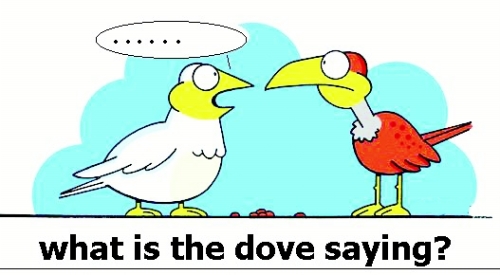 |
What is the dove saying? |
英语在成为全球语言的道路上做到了“两手都硬”,即以经济、军事为代表的硬实力与以政治影响、社会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相结合。正是这股强大的力量,支撑着英语文化的世界地位。
我们这一代在北京上学的90后,至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习英语,算到初三义务教育结束,也少说有6年的英语学习经验,更不必说那些在大学里读英语系的同学们。若是将90后再细分到95后,我们会发现身边为数不少的95后们在中学就打起了出国深造的主意,而英语更是他们学习的大头。
“为什么我们要学英国话,而老外就不把中文当做必修科目?”这个问题是我小时候经常挂在嘴边的,中学以后就不再问了。原因很简单,为了分数啊!
日后我又考进了英语系,学着学着,在听了多种奇奇怪怪的英语并且发现身边有同学对“英音”有着极致追求时,我产生了又一个问题:我学的是英语还是英国话?
大卫·克里斯特尔在《英语:全球语言》一书中提出观点,英语是一种“全球语言”,而英语获得“全球语言”的定位的原因在于其历史演进、文化基础与文化内涵的综合作用。
具体来讲,在历史方面,英语国家占据了殖民时代、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的先机。如果说在殖民时代,庞大的法语殖民地还可以与日不落帝国一较高下,那么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这一英语文化巨人的快速崛起,法语世界便逐渐落了下风。至于在信息时代,星条旗更是处在一个全球领先的高度。地球人上网搜的网址都是英文的,英语又怎么能不占据全球地位呢?
而在文化方面,大英帝国身后辽阔的海外殖民地在各自独立之后,或出于历史文化原因,或出于维持国内拥有民族语言的各民族稳定的愿望,英语成为了这些独立国家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这为英语文化的全球化进程再添一笔。此外,诸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传媒方式及电报、电话等交流方式在英美等英语国家或率先出现,或大为发展。这同时也在为拓展英语文化与英语本身的全球化添砖加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英语在成为全球语言的道路上做到了“两手都硬”,即以经济、军事为代表的硬实力与以政治影响、社会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相结合。正是这股强大的力量,支撑着英语文化的世界地位。
英语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全球语言地位的语种吗?有人会说在英语之前还有过拉丁语。拉丁语在人类科学发展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如同每一种得到科学认可的动植物都有一个拉丁语名称一样。但拉丁语流行的时期,世界还不完全是世界,这个星球可以是欧洲人的世界,也可以是中国人的世界。而英语“统治”下的世界,则是一个互联沟通的时空,无论是借由天上、地上、海上的三维交通,还是虚拟的网络平台。英语正是通过控制对信息渠道的支配权将它自己的能量渗透入各个与世界交联的地方文化圈中。
从这个角度看,英语在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被英语影响的文化体系也在塑造着英语本身。
大卫·克里斯特尔将英语的影响划分为三个圈子。最核心的一圈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以英语为原生语言的国家;第二个圈子是诸如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一类以英语为通用语言的国家;第三个圈子则是像中国一样将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国家。这三个圈子涵盖了世界上多数国家,体现着英语强势的全球地位。与此同时,大卫·克里斯特尔也提醒我们注意这三个圈子中不同的地域语言文化正在改变着英语。
在第一个圈子中,英语原生语言的地位正在受到挑战。特别是在以文化多样性著称的美国,拉丁裔人口的增长使得西班牙语在美国的地位逐年上升,甚至于有预测称以西班牙语为原生语言的美国人会最终超过美国的英语人口。这一变动也在美国国内掀起了“要不要设立官方语言”的争论。此外,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这些国家中,由于文化发展差异,其语言内涵差异也在拉大。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在一场国际会议上,热爱棒球运动的美国人用棒球规则设喻,引得其他国家代表一头雾水,英国代表随即以板球运动规则回答,于是一场严肃的国际会谈变成了对运动规则的讨论。
而在第二和第三个圈子中,英语则逐渐和当地语言融合,演变出各种各样的“lish”,比如我们最熟悉的“Chinglish”,还有让英语专业学生在听力考试中闻之色变的印度英语,等等。我们曾以“Chinglish”为英语教育中的反面教材,但语言学家却将这种“地方化世界语言”作为一种正常现象进行研究。“全球语言”这一地位正逐渐地让英语从单一的语言发展为一个语言的集合体。新的词汇不断汇入,语法规则不断更改,发音规律也各自不同。各色的地方英语在为英语这一概念带来更旺盛的生命力的同时,也让英语的未来充满着变数。
全世界都在说英语,但全世界并不都在说英国话。英国话之于英语的概念,如同山东话之于汉语的概念,仅仅是这个大的语言家族中的一个方言。
还记得在语音课上,老师问大家倾向于英音还是美音,问到我这里时,我站起来故意用带着京片子味儿的英语说道:“我为我的北京英语而自豪”,当时也就是想给同学们逗个乐。现在看来,我这是在为英语的全球化发展做贡献啊!
作者系外交学院英语系翻译专业学生
英语在成为全球语言的道路上做到了“两手都硬”,即以经济、军事为代表的硬实力与以政治影响、社会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相结合。正是这股强大的力量,支撑着英语文化的世界地位。
我们这一代在北京上学的90后,至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习英语,算到初三义务教育结束,也少说有6年的英语学习经验,更不必说那些在大学里读英语系的同学们。若是将90后再细分到95后,我们会发现身边为数不少的95后们在中学就打起了出国深造的主意,而英语更是他们学习的大头。
“为什么我们要学英国话,而老外就不把中文当做必修科目?”这个问题是我小时候经常挂在嘴边的,中学以后就不再问了。原因很简单,为了分数啊!
日后我又考进了英语系,学着学着,在听了多种奇奇怪怪的英语并且发现身边有同学对“英音”有着极致追求时,我产生了又一个问题:我学的是英语还是英国话?
大卫·克里斯特尔在《英语:全球语言》一书中提出观点,英语是一种“全球语言”,而英语获得“全球语言”的定位的原因在于其历史演进、文化基础与文化内涵的综合作用。
具体来讲,在历史方面,英语国家占据了殖民时代、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的先机。如果说在殖民时代,庞大的法语殖民地还可以与日不落帝国一较高下,那么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这一英语文化巨人的快速崛起,法语世界便逐渐落了下风。至于在信息时代,星条旗更是处在一个全球领先的高度。地球人上网搜的网址都是英文的,英语又怎么能不占据全球地位呢?
而在文化方面,大英帝国身后辽阔的海外殖民地在各自独立之后,或出于历史文化原因,或出于维持国内拥有民族语言的各民族稳定的愿望,英语成为了这些独立国家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这为英语文化的全球化进程再添一笔。此外,诸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传媒方式及电报、电话等交流方式在英美等英语国家或率先出现,或大为发展。这同时也在为拓展英语文化与英语本身的全球化添砖加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英语在成为全球语言的道路上做到了“两手都硬”,即以经济、军事为代表的硬实力与以政治影响、社会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相结合。正是这股强大的力量,支撑着英语文化的世界地位。
英语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全球语言地位的语种吗?有人会说在英语之前还有过拉丁语。拉丁语在人类科学发展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如同每一种得到科学认可的动植物都有一个拉丁语名称一样。但拉丁语流行的时期,世界还不完全是世界,这个星球可以是欧洲人的世界,也可以是中国人的世界。而英语“统治”下的世界,则是一个互联沟通的时空,无论是借由天上、地上、海上的三维交通,还是虚拟的网络平台。英语正是通过控制对信息渠道的支配权将它自己的能量渗透入各个与世界交联的地方文化圈中。
从这个角度看,英语在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被英语影响的文化体系也在塑造着英语本身。
大卫·克里斯特尔将英语的影响划分为三个圈子。最核心的一圈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以英语为原生语言的国家;第二个圈子是诸如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一类以英语为通用语言的国家;第三个圈子则是像中国一样将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国家。这三个圈子涵盖了世界上多数国家,体现着英语强势的全球地位。与此同时,大卫·克里斯特尔也提醒我们注意这三个圈子中不同的地域语言文化正在改变着英语。
在第一个圈子中,英语原生语言的地位正在受到挑战。特别是在以文化多样性著称的美国,拉丁裔人口的增长使得西班牙语在美国的地位逐年上升,甚至于有预测称以西班牙语为原生语言的美国人会最终超过美国的英语人口。这一变动也在美国国内掀起了“要不要设立官方语言”的争论。此外,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这些国家中,由于文化发展差异,其语言内涵差异也在拉大。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在一场国际会议上,热爱棒球运动的美国人用棒球规则设喻,引得其他国家代表一头雾水,英国代表随即以板球运动规则回答,于是一场严肃的国际会谈变成了对运动规则的讨论。
而在第二和第三个圈子中,英语则逐渐和当地语言融合,演变出各种各样的“lish”,比如我们最熟悉的“Chinglish”,还有让英语专业学生在听力考试中闻之色变的印度英语,等等。我们曾以“Chinglish”为英语教育中的反面教材,但语言学家却将这种“地方化世界语言”作为一种正常现象进行研究。“全球语言”这一地位正逐渐地让英语从单一的语言发展为一个语言的集合体。新的词汇不断汇入,语法规则不断更改,发音规律也各自不同。各色的地方英语在为英语这一概念带来更旺盛的生命力的同时,也让英语的未来充满着变数。
全世界都在说英语,但全世界并不都在说英国话。英国话之于英语的概念,如同山东话之于汉语的概念,仅仅是这个大的语言家族中的一个方言。
还记得在语音课上,老师问大家倾向于英音还是美音,问到我这里时,我站起来故意用带着京片子味儿的英语说道:“我为我的北京英语而自豪”,当时也就是想给同学们逗个乐。现在看来,我这是在为英语的全球化发展做贡献啊!
作者系外交学院英语系翻译专业学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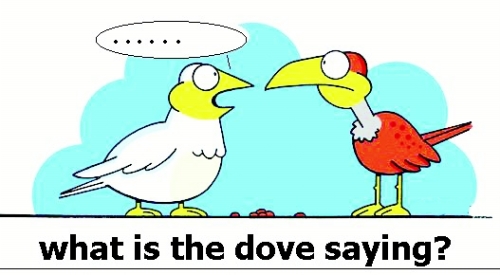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