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冷血动物一起探索自然
○作者 [英] 帕特里克·巴克汉姆 ○译者 韦盖利
《
青年参考
》(
2014年05月21日
32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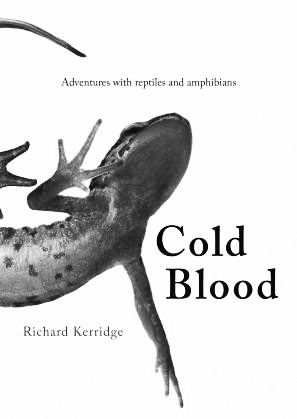 |
《冷血动物》(Cold Blood),查托与温达斯出版社2014年5月,304页。 |
在自然界,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只是池塘与草丛中的小角色;但另一方面,它们具有特定的文化含义,影响着人类的进化,并在我们儿时的记忆中占据一席之地。
如今,市面上描写自然的作品汗牛充栋、良莠不齐。黄蜂、蝴蝶、田野、沼泽、鱼鹰、乌鸦、野草、小径……看起来,没有哪类生物或哪个角落值得用几十万字去写。
似乎每个城里人都会断言,仔细研究蜗牛,也能出一本关于蜗牛的书。作为其中之一,我就写过有关獾和蝴蝶的科普读物;另一位书评家讥讽道:“忏悔式”的自然写作流行,就如伦敦北部农贸市场增多在文学意义上的等量反映。不过,把《冷血动物》的面世称为这种随大流的出版气候的又一表现,是有失公平的。用蛇行一样流畅的文笔,作者理查德·克里奇完成了一部关于他与蝾螈、青蛙、蜥蜴和蛇的回忆录,轻描淡写间透着智慧的闪光。
作者在本书开头描述了童年的激情,这是自然题材写作中常见的。但克里奇在与家人散步时发现一只金色蝾螈的奇遇,对建立他与父亲复杂关系的情感基调非常重要。笔者对蝴蝶的爱是伴着与父亲的和谐关系产生的,但克里奇对蝾螈的迷恋源于对长辈的逆反心理。上世纪60年代,在别的孩子爬树掏鸟蛋、到小溪里抓鱼的时候,克里奇居住在一个爬行动物很少(通常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地方,但他在书中写到,“如果足够靠近地面,你还是有机会看到‘森林’和‘草原’,看到跟你的识物卡上一样奇怪、美丽和凶猛的生灵的。”
克里奇喜欢捕捉蝾螈、青蛙和蛇,这并未让他成为一个怪人,却因此交了不少朋友,小伙伴们挥舞着白色短裤做成的网去捕捉动物。通过他们跟克里奇之父吵架、捉迷藏的经历,我们了解了那些活在常常被忽视的草地上、池塘里和小溪间的“居民”的趣味生物学知识。
克里奇的第一次捕捉以悲剧收场。他发现了一只蝾螈的尸体,它是在逃出牢笼后窒息而死的。当时他并不知道,这种动物的皮肤在显微镜下呈网状,把各种器官包裹在里面,氧气通过网眼直接进入它们的血液,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则从网眼中释放出来。两栖动物用肺呼吸的同时还用皮肤呼吸,它们的皮肤可以被水渗透,若长时间缺水,必然一命呜呼。
《冷血动物》在探究蟾蜍的生物学和文化学角色时尤为精彩。这种花园里常见的笨拙动物一度被视为魔鬼的化身,18世纪博物学家托马斯·彭南特把蟾蜍描述成“最畸形、最丑陋的动物”。蟾蜍在春季的交配仍是让人困扰的谜:雄蟾蜍在池塘里聚集,五六位男士争夺一位女士,像球一样狂乱地滚动,常常会把雌蟾蜍溺死,甚至把青蛙和鱼卷入其中。
无怪乎,当奥赛罗错误地怀疑妻子苔丝德蒙娜有地下情时,他顿时感到自尊扫地,觉得生命的河流干涸了,变成了“邪恶的蟾蜍的水塘……任它们在水中交欢”。
相比之下,蛇曾经指代的概念更为繁多。在《圣经》里,“蛇是人类环境的助产士”,如克里奇所言——让我们走向诱惑。进化论心理学的创始人、伟大的爱蛇者艾德华·奥·威尔森则发现,蛇是人类梦境里出现最多的动物。另一批科学家认为,人类的进化深受对蛇的警惕的影响——罗杰·乌尔里希通过试验发现,多次给人们看蛇、蜘蛛的照片,以及手枪、磨损的电线等图片,受试者很快会忘记其他的潜在危险,但对蛇的恐惧从来不会消失。
对蛇的厌恶,也是因为我们不仅把蛇看成生理上的冷血动物,还相信它们精于算计、没有同情心。关于蛇的外表,克里奇在书中写道:“人们认为它的外貌背后没有慈爱,没有疑问,没有好奇、惊讶,或害怕。”大多数蛇潜伏在树丛里捕食,等待,选择合适时机进攻。但克里奇指出,它们根本没有什么“阴谋诡计”,只是我们觉得它们是那样而已。我们应该更理性地看待蛇,将它们视作“对周围的环境极其敏感,具有我们的感官所没有的敏锐”。
克里奇对冷血动物的喜爱,帮助他逃脱了父亲的苛责,让他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对自身经历的回忆,让这本书娴熟地平衡了科普、回忆录、文化探索等元素,并有了动人的结尾——《冷血动物》带我们认识这些小生灵的奇妙之处,并深刻地探究了人类与它们的关系。
□英国《卫报》

在自然界,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只是池塘与草丛中的小角色;但另一方面,它们具有特定的文化含义,影响着人类的进化,并在我们儿时的记忆中占据一席之地。
如今,市面上描写自然的作品汗牛充栋、良莠不齐。黄蜂、蝴蝶、田野、沼泽、鱼鹰、乌鸦、野草、小径……看起来,没有哪类生物或哪个角落值得用几十万字去写。
似乎每个城里人都会断言,仔细研究蜗牛,也能出一本关于蜗牛的书。作为其中之一,我就写过有关獾和蝴蝶的科普读物;另一位书评家讥讽道:“忏悔式”的自然写作流行,就如伦敦北部农贸市场增多在文学意义上的等量反映。不过,把《冷血动物》的面世称为这种随大流的出版气候的又一表现,是有失公平的。用蛇行一样流畅的文笔,作者理查德·克里奇完成了一部关于他与蝾螈、青蛙、蜥蜴和蛇的回忆录,轻描淡写间透着智慧的闪光。
作者在本书开头描述了童年的激情,这是自然题材写作中常见的。但克里奇在与家人散步时发现一只金色蝾螈的奇遇,对建立他与父亲复杂关系的情感基调非常重要。笔者对蝴蝶的爱是伴着与父亲的和谐关系产生的,但克里奇对蝾螈的迷恋源于对长辈的逆反心理。上世纪60年代,在别的孩子爬树掏鸟蛋、到小溪里抓鱼的时候,克里奇居住在一个爬行动物很少(通常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地方,但他在书中写到,“如果足够靠近地面,你还是有机会看到‘森林’和‘草原’,看到跟你的识物卡上一样奇怪、美丽和凶猛的生灵的。”
克里奇喜欢捕捉蝾螈、青蛙和蛇,这并未让他成为一个怪人,却因此交了不少朋友,小伙伴们挥舞着白色短裤做成的网去捕捉动物。通过他们跟克里奇之父吵架、捉迷藏的经历,我们了解了那些活在常常被忽视的草地上、池塘里和小溪间的“居民”的趣味生物学知识。
克里奇的第一次捕捉以悲剧收场。他发现了一只蝾螈的尸体,它是在逃出牢笼后窒息而死的。当时他并不知道,这种动物的皮肤在显微镜下呈网状,把各种器官包裹在里面,氧气通过网眼直接进入它们的血液,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则从网眼中释放出来。两栖动物用肺呼吸的同时还用皮肤呼吸,它们的皮肤可以被水渗透,若长时间缺水,必然一命呜呼。
《冷血动物》在探究蟾蜍的生物学和文化学角色时尤为精彩。这种花园里常见的笨拙动物一度被视为魔鬼的化身,18世纪博物学家托马斯·彭南特把蟾蜍描述成“最畸形、最丑陋的动物”。蟾蜍在春季的交配仍是让人困扰的谜:雄蟾蜍在池塘里聚集,五六位男士争夺一位女士,像球一样狂乱地滚动,常常会把雌蟾蜍溺死,甚至把青蛙和鱼卷入其中。
无怪乎,当奥赛罗错误地怀疑妻子苔丝德蒙娜有地下情时,他顿时感到自尊扫地,觉得生命的河流干涸了,变成了“邪恶的蟾蜍的水塘……任它们在水中交欢”。
相比之下,蛇曾经指代的概念更为繁多。在《圣经》里,“蛇是人类环境的助产士”,如克里奇所言——让我们走向诱惑。进化论心理学的创始人、伟大的爱蛇者艾德华·奥·威尔森则发现,蛇是人类梦境里出现最多的动物。另一批科学家认为,人类的进化深受对蛇的警惕的影响——罗杰·乌尔里希通过试验发现,多次给人们看蛇、蜘蛛的照片,以及手枪、磨损的电线等图片,受试者很快会忘记其他的潜在危险,但对蛇的恐惧从来不会消失。
对蛇的厌恶,也是因为我们不仅把蛇看成生理上的冷血动物,还相信它们精于算计、没有同情心。关于蛇的外表,克里奇在书中写道:“人们认为它的外貌背后没有慈爱,没有疑问,没有好奇、惊讶,或害怕。”大多数蛇潜伏在树丛里捕食,等待,选择合适时机进攻。但克里奇指出,它们根本没有什么“阴谋诡计”,只是我们觉得它们是那样而已。我们应该更理性地看待蛇,将它们视作“对周围的环境极其敏感,具有我们的感官所没有的敏锐”。
克里奇对冷血动物的喜爱,帮助他逃脱了父亲的苛责,让他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对自身经历的回忆,让这本书娴熟地平衡了科普、回忆录、文化探索等元素,并有了动人的结尾——《冷血动物》带我们认识这些小生灵的奇妙之处,并深刻地探究了人类与它们的关系。
□英国《卫报》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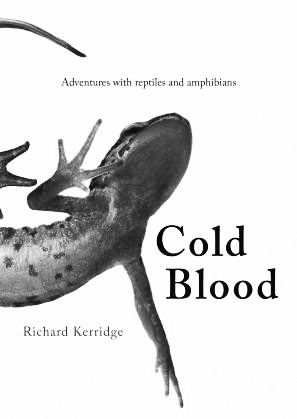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